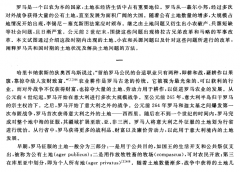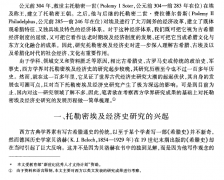罗马统治时期希腊人的民族认同
【作者简介】徐晓旭,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武汉 430079)
【内容提要】 在罗马统治下,希腊人虽然丧失了政治独立,但作为一个“文化民族”仍葆有其传统的民族认同。这种认同的内容主要有对于自身血缘、语言、宗教和生活方式的同一性的认同、希腊人—蛮族人两极对立的观念、对于希腊化的非希腊人的认同。在内容没有根本变化的同时,希腊民族认同的实现方式却发生了若干复杂而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的一个共性就是,在接受和适应罗马统治的前提下,将自身认同的主方向定为更加强调文化和历史传统。继后的“罗马人”和基督教徒身份认同成为拜占庭时期希腊民族认同的主体内容。
【关 键 词】民族认同/希腊人/希腊化/罗马/基督教化
直到目前为止,罗马统治时期的希腊世界仍处在国内希腊史和罗马史研究领域之间的“两不管”地带。造成这种状况的潜在原因,也许是人们通常以国家为古代文明研究单位的学术传统:罗马的征服使希腊城邦和希腊化王国的主权不复存在,希腊史于是至晚写到希腊化时代为止;而罗马史的撰写和研究又以罗马国家的发展为显性或隐性的主轴,对罗马时代希腊人情况的描述至多也不过是蜻蜓点水,更谈不上有以希腊人为本位的系统论著。然而,无论从希腊史还是从罗马史角度而言,罗马时代的希腊人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研究对象,希腊古典文化中的不少成就是他们创造的。而他们何以能够并且究竟怎样保持自己的民族存在和认同,无疑是理解他们这段历史和这些成就的最重要问题之一。
本文即是对上述问题的一项尝试性研究,其任务在于利用有关史料力图复原罗马时代希腊人民族认同的总体情形并侧重从以下角度入手:(1)罗马时代希腊人的民族认同与希腊人以前的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2)罗马人和希腊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对希腊人民族认同的影响;(3)希腊人的民族认同在古代晚期的最终走向。
二战后,无论是西方、苏联—俄罗斯,还是中国、日本,国际学术界在“民族”界定问题上都经历了一个大体一致的理论转向,即由先前以民族国家为衡量标准、用nation和nationality来指称民族,日益转向将ethnos、ethnic group与nation、nationality区分开来,用ethnos和ethnic group 来指称不必依赖国家来定义的各种民族。①
那么古代希腊人是如何被指称为“民族”的呢?19世纪和20世纪大半个时期内,很多西方古典学家都习惯于将古代希腊人视为一个力图实现、却未能实现政治统一的nation,还有学者专门探讨能否将nation和nationality用于希腊人身上。如到20世纪70年代著名古典学家芬利还曾谈道:“如果我们坚持将民族(nation)与民族国家(nation-state)等同起来的话,那么希腊人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才是一个民族呢?”② 而如今,将古代希腊人作为一个ethnic group 考察其民族认同已成为古典学领域内的一个研究热点。本文提到的古代希腊人的“民族”即相当于西文中的ethnic group;相应地,“民族认同”则相当于ethnic identity和ethnicity。
不过,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表述与民族学理论的话语系统也并非完全对等,这就造成了对译上的困难。以往中国通常用“民族”一词来翻译西文中各种不同类型的民族。近些年来,随着从西方民族学和人类学界引进的ethnic group流行开来,国内学术界对之有“民族”、“民族群体”、“民族集团”、“种族”、“族裔群体”等多种译法,目前“族群”这一来自港台学界的译法日益呈现出可能会取代其他译法的趋势。但是,笔者并未采用这一译法,而是采用了较保守的“民族”译法,这首先是考虑到本文所要论述的是希腊人整个群体的认同,而在西方古典学界,不仅希腊人整个群体被称为ethnic group,而且希腊人的各个分支,如伊奥尼亚人、多里斯人、彼奥提亚人等,也都被称为ethnic group,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使用“希腊人的族群认同”这样的提法,也有可能使人误以为本文要讨论的是希腊人内部亚群体自身的认同。作为最大规模的ethnic group, 希腊人的整个群体恰恰适合于用汉语的“民族”一词来表达。
其次,从古代希腊人和现代希腊人的话语系统来看,古希腊语中ethnos一词在不同语境中能够指称大致相当于现代语言中所说的“民族”、“部族”、“部落”、“国民”(当然是指城邦公民)等不同规模的人群,其用法与现代西文中ethnic group的较宽泛用法类似,即能够指称多种规模的“族群”,而它所指的最大规模的族群正是民族;在现代希腊语中,ethnos则兼具nation和ethnic group两方面的含义,又恰巧在语义上与汉语“民族”一词相符。③ 所以,至少在本文的汉语表达中,选择“民族”这一传统名词来指称古代希腊人的整个群体,要比使用“族群”这一新名词更能接近古代希腊人自身的话语表述。
一
在罗马统治下,希腊人虽然丧失了政治独立,但并没有像同样被罗马征服的西部地中海世界诸民族一样罗马化,而是仍作为一个“文化民族”将其传统的民族认同一直保持到罗马帝国基督教化前夕为止。④
罗马时代希腊人所继承的民族认同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对于自身血缘、语言、宗教和生活方式同一性的认同;希腊人—蛮族人两极对立的观念;对于希腊化的非希腊人的认同。这些内容依次形成于古风时代(公元前776—前480年)、古典时代(公元前480—前323年)和希腊化时代(公元前323—前31年), 虽然形成的次序不同,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意识形态体系。
在公元前8世纪末叶至公元前6世纪中叶这一期间,Hellenes(“希腊人”)由一支希腊部落的名称演变为全体希腊人的总称。这一民族总称本身当然也是各部落和各城邦的希腊人在它之下确立认同的最鲜明的标记。在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希腊人对于自身认同的各种行为和话语当中,最具经典性的表述恐怕莫过于希罗多德的一句话:“to Hellenikon, eon homaimon te kai homoglosson, kai theon hidrymata te koina kai thysiai ethea te homotropa 。 ”⑤ 其中的 to Hellenikon既可以理解为“希腊人”,也可以理解为“希腊特性”这一抽象意义。在后一种意义上,它相当于现代西方语言中的Greekness, Greekhood, Hellenicity, grécité等词。这样,这句话就既可以译作“希腊人有相同的血缘、相同的语言、共同的神庙、祭礼和共同的习俗”,也可以译作“希腊特性是相同的血缘、相同的语言、共同的神庙、祭礼和共同的习俗”。显然,系动词“是”(eon)和系表句式使这句话看起来很像一个关于“希腊人”或“希腊特性”的定义。
民族认同不仅是一个认同“自我”(self)的问题,还是一个对“自我”与“他者”(other)即其他民族加以区分的问题。更多的学者认为,公元前5世纪早期,barbaroi(此为复数,单数为barbaros)由原来一个偶然用于嘲笑外族语言的词语最终演变为一个同“希腊人”相对立的概念,构成对一切非希腊人的蔑称。⑥ 希腊人眼中的这种barbaroi不会说希腊语,缺乏理性;缺乏政治自由,由暴君统治;丧失节制,荒淫无度,野蛮凶残;天生具有奴性;等等。我们在汉语中通常将这个barbaros译为“蛮族人”。促成希腊人—蛮族人两极对立观念形成的最根本因素是希波战争。这场战争是希腊人第一次成功地抵抗外敌入侵的泛希腊主义联合行动。外来威胁和抗战的胜利促使希腊人转到侧重于从外部,从“他者”,从非希腊人角度来进行自我定义。⑦
早在古典时代后期,伊索克拉底在谈到当时尚属个别的希腊化现象时,就已经预言到希腊化时代希腊人对希腊化的蛮族人愈加普遍的认同:“‘希腊人’这个名字已不再表现为一个种族(genos)的名称,而是一种智力(dianoia)的名称了;与其把与我们出身(physis)相同的人叫做‘希腊人’,不如把拥有我们的文化(paideusis)的人叫做‘希腊人’。”⑧ 在希腊化各王国统治者以希腊文明作为统治的文化基础的情况下,接受希腊教育和文化,会说希腊语,奉行希腊宗教和生活方式的非希腊人越来越多,他们也越来越多地被认同为希腊人。⑨ 语言、宗教和生活方式这些东西实质上都构成了“文化”的具体内容,其认同总括而言便是一种文化认同。
希腊人素来就是一个典型的“文化民族”,其同一性从来不依赖于政治统一,因而其传统的民族认同内容并未因罗马的统治而改变。由于希腊文化自身的影响和罗马对它的支持,希腊化进程在罗马时代并没有停止,反而获得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扩大。例如,加拉太人是迁居到小亚细亚的一支高卢人,他们的希腊化就发生在罗马时代。一直到古代晚期,罗马帝国东部各行省社会上层和知识分子中的一大部分都是希腊化的非希腊人。
“希腊人”这个族名在罗马时代的使用情况与在希腊化时代并无二致。被称为“希腊人”者既有种族上的希腊人,也有希腊化的非希腊人。罗马在希腊本土设置了阿凯亚(Achaia)行省,但是没有希腊人因此而自称“阿凯亚人”。⑩ 马其顿人在希腊化时代以前没有被视为希腊人,在罗马时代的铭文中则被明确地列为希腊人的一个部落:“马其顿人和其他希腊部落”(Makedosin kai tois loipois ethnesin tois Hellenikois)。“亚细亚的希腊人”(tois epi tes Asias Hellesin)、“亚细亚的希腊人共同体”(koinon ton epi tes Asias Hellenon)、“比提尼亚的希腊人共同体”(koinon ton en Beithyniai Hellenon)等提法均见于小亚细亚出土的罗马时代的铭文。(11) 在称某人为“希腊人”时,人们有时也会提及其原初的种族,而无论他是否出身于希腊种族。一位名叫奥林匹娅(Olympia)的希腊妇女曾客居并死于罗马, 其兄弟给她树立的墓志铭中写道:“种族(genos)上属希腊人,我的故乡是阿帕美亚(Apamea)”。(12) 而《新约·马可福音》讲到耶稣在推罗边境遇到一个妇女求他驱除附在她女儿身上的污鬼时则说:“这个妇女是一个希腊人,在种族(genos)上是一个叙利亚腓尼基人。”(13) 由后一例可见,对于希腊化的非希腊人的希腊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并没有受到其非希腊出身的贬损。
罗马统治时期希腊人对于“希腊人”或“希腊特性”的理解和表述也几乎是对以往同类话语的重申。在公元前1世纪的哈利卡尔那索斯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os Halikarnasseus)看来,“希腊特性”的内容是“说希腊语”,奉行“希腊人的习俗”,“承认同样的神祇”和“适当公平的法律”等; “希腊本性(physis Hellas)主要是依据这些而有别于蛮族本性的。”他认为居住在黑海沿岸的阿凯亚人原属埃利斯人,其起源是“最希腊的”(Hellenikotatos),但他们“现在是所有蛮族人中的最野蛮者”。(14)
智者兼哲学家法沃里努斯(Favorinus,约公元85—155年)是一位“希腊化的高卢人”。(15) 他以第三者的口吻反复论证自己的希腊特性。他谈到自己“不仅曾力争掌握希腊人的语言(phone),而且曾力争获得希腊人的心智(gnome)、生活(diaita)和方式(skhema)。”他认为自己在这些方面的“努力和显著成绩”是“在他之前的罗马人和他那个时代的希腊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的。他表白了自己渴望成为希腊人的心态:“可以看到,最好的希腊人在罗马倾心于罗马人的行为方式,而他却倾心于希腊人的行为方式,并为此完全放弃了财产、政治名望和一切,他做这一切只为一个目的——使他不仅像(dokein)个希腊人,而且就是(einai)希腊人”;“他虽是罗马人,但已经完全希腊化了”。他将自己视为一位“文化希腊人”的成功范例,并且希望因此获得希腊人的认同和为自己高卢同胞的希腊化提供激励:“对于希腊人来说,希腊的本地人有了一个文化与出身之于名誉并无区别的例子”;“对于凯尔特人来说,若是看看这个人,就没有一个人会丧失接受希腊文化的信心了。”(16)
从内容上看,上述两人对“希腊人”和“希腊特性”的界定大致相同。同希罗多德的“希腊人”“定义”相比,两人的界定都缺少共同的血缘一项。就其他方面内容而言,两人的界定或多或少都有与希罗多德的“定义”相重合的地方。而这些内容又都与伊索克拉底所说的“文化”相吻合。狄奥尼修斯虽未明确提到“文化”一词,但他对黑海沿岸的阿凯亚人的看法,无疑为伊索克拉底以文化作为希腊人的定性标准的论断提供了例证。法沃里努斯使用的“出身”(phynai)、“文化”(paideuthenai, paideia)和“心智”(gnome)等词与伊索克拉底使用的“出身”(physis)、“文化”(paideusis)和“智力”(dianoia)等词之间的同源关系或相似性更是显而易见的;两人使用这些词的论证也存在着某些相通之处。从身份上看,狄奥尼修斯在种族上就是希腊人,法沃里努斯则是希腊化的非希腊人;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代表了当时被称为“希腊人”的构成。这种拥有希腊血统的希腊人和希腊化的非希腊人以希腊文化为基础的认同,无疑是希腊化时代希腊民族认同特质的自然延续。
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看起来似乎有些矛盾的是,在对希腊化的非希腊人的文化认同越来越普遍的同时,希腊人传统的血缘认同并未因此被完全忘记,它仍在某些场合被表达出来,甚至被加以强调。很可能出自公元前3 世纪克里特的海拉克雷戴斯(Herakleides Kretikos)之手的一则残篇说:“希腊人是种族(genos)上为希伦的后代、说希腊语的人。居住在阿提卡的雅典人在种族(genos)上是阿提卡人,说阿提卡方言,正如多里斯人是多罗斯的后代,在语言上说多里斯方言,爱奥洛斯的后代说爱奥利斯方言,由克苏托斯(Xouthos)之子伊翁所生(phyntes)的人说伊奥尼亚方言。”(17) 这段希腊化时代的言论不免令人想到成书于公元前580—540年的(伪)赫西俄德(Ps. Hesiodos)的《名媛录》(Gynaikon katalogos, Eoiai)中讲到的希伦家族谱系:希伦生子多罗斯、克苏托斯和爱奥洛斯,克苏托斯生子阿凯奥斯和伊翁。(18) 两则史料的说法大体相同,叙事方式也一样,都是从血缘角度以神话话语来定义希腊人的几大方言部落之间的差别和认同。希伦(Hellen)、多罗斯(Doros)、爱奥洛斯(Aiolos)、阿凯奥斯(Akhaios)和伊翁(Ion)分别是希腊人和多里斯人(Dorieis)、爱奥利斯人(Aioleis)、阿凯亚人(Akhaioi)和伊奥尼亚人(Iones)这几大方言部落的命名祖先。
在罗马时代,血缘认同的传统仍在希腊人当中延续。罗马皇帝哈德良应某些希腊城市的要求,建立了一个全体希腊人的组织——“泛希腊同盟”(Panhellenion)。关于入盟资格,学者对史料的解读存在分歧。S. 斯万(S. Swain)认为, 相关的史料表明,有入盟意图者须证明与罗马之间的长期友好关系和在种族及文化方面的希腊特性。(19) 而J. M. 豪尔(J. M. Hall)则指出,现存涉及入盟标准的史料事实上只强调了希腊血统(genos Hellenikon)。(20) 的确,同希腊化时代的情形一样,某些入盟城邦实际上是由希腊化的非希腊人构成的,但它们为了证明自己具备入盟资格,就采用虚构的血缘谱系来追溯与希腊本土的关系。例如,辛那达(Synnada)本是希腊化的弗吕吉亚城市,却自称是由斯巴达人和雅典人合建的。基比拉(Kibyra)居民的祖先主要是吕底亚人,他们却声称基比拉是斯巴达人建立的殖民地,同雅典人也有亲缘关系。
当血缘被选择作为一种民族认同的标准、标志、内容和话语方式的时候,它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生物学和遗传学名词,而是变成一个负载着文化内容的社会性名词了。所谓民族的共同血缘,实际上既有现实的成分,也有想像的成分,而历史的发展又往往会令两者混淆不清。希腊化和罗马时代希腊人的血缘认同,表面上看处在对希腊化的非希腊人的文化认同的对立面,实则构成这一文化认同的潜在的选择性成分。希腊化的非希腊人突破血缘标准这一障碍并非难事,只需在文化上虚构其希腊血缘和谱系并使之得到希腊人的认可即可。
各方面希腊特性的保持和强调,也意味着罗马时代希腊人鄙视非希腊人并带有文化沙文主义的“蛮族”观念一如既往。公元2世纪, 亚述人塔提亚诺斯在其攻击希腊文化及哲学和颂扬基督教的著作《致希腊人》中开篇就呼吁道:“希腊人哪,不要对蛮族人这么怀有敌意,也不要鄙视他们的思想。你们的风俗有哪一样不是源自蛮族?”(21) 塔提亚诺斯本人的身份有些复杂,他早年是一个热衷于学习希腊文化和哲学的希腊化的非希腊人,中年时出于对希腊思想和宗教的不满和反感皈依了基督教,晚年又与罗马教会决裂。《致希腊人》的写作时间是在他皈依基督教后不久,此时他这种不免过激的反希腊文化言论却很能反衬出希腊人对非希腊人鄙视的程度。
二
希腊人的民族认同在罗马统治的大部分时期中其内容没有根本变化的同时,实现方式却发生了若干复杂而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的一个共性就是:在接受和适应罗马统治的前提下,将自身认同的主方向定为更加强调文化和历史传统。面对当代的屈辱和无力,他们需要在回顾和重温祖先的荣光中得到安慰。在独立和主权失落后,他们需要从自己本已享有崇高地位的文化中找寻更多的自豪。
作为失败者和被统治者,希腊人对罗马人的心理反应是非常复杂和充满矛盾的。E. S. 格鲁恩将希腊人对罗马扩张的态度描述为“有仇恨,也有钦佩、惧怕、感激、愤怒、失望,尤其还有慌乱”。(22) 这是罗马刚开始对希腊世界征服时期希腊人的心理反应,不过它已经奠定了日后希腊人对待罗马统治的心理基调。被罗马征服和统治以后,除了上述绝大部分心情外,希腊人对待罗马人的态度中至少又增加了屈从和不时的逢迎。我们仅从“罗马”和“罗马人”这些名称在希腊人中间曾经带来的两种不同凡响中,就可以感受到希腊人内心的矛盾。
罗马介入希腊化世界不久,某些罗马人个体、罗马人集体和女神“罗马”(Roma)就开始被一些希腊城邦冠以“恩主”的称誉并加以崇拜。在公元前196 年的地峡竞技会上,罗马代行执政官提图斯·昆克提优斯·弗拉米尼努斯(Titus Quinctius Flamininus)派传令官宣布希腊人获得自由。他因此举而受到希腊人的爱戴,希腊各处都发现了向他致以敬意的铭文。很多希腊城市的文件中都将罗马人称作“共同的恩主”。最为普遍的是对女神“罗马”的崇拜。该崇拜有时还伴以对罗马人民(demos)的崇拜。自公元前189年在德尔菲设立的第一个祭祀女神“罗马”的“罗马节”(Rhomaia)以来,已知在公元前2世纪至少有13个城邦设立了这一宗教节日。罗马最初是以希腊化王国国王的反对者和希腊人的解放者形象出现在希腊世界的,很多希腊城邦将它视为保护者而与之结盟。罗马势不可挡的武力和征服又给希腊人以强烈的震撼。希腊人长期受制于希腊化各统治者和国王,已经习惯于将更强的政治势力接受为保护者并加以崇拜的做法,面对比希腊化各王国更为强大的罗马,就更容易抱有接受其保护的心态。宗教是这种心态的便利的表达途径。Roma(“罗马”)一词的希腊语是Rhome,恰恰与希腊语rhome(“力量”)词形相同。女神“罗马”在希腊人意识当中是罗马力量人格化的体现,赋予她以“恩主”的称号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罗马保护者地位的认同。(23)
曾被希腊人赋予“恩主”的同一个“罗马人”之名也会成为希腊人的怨府。《西比拉神谕》透露了希腊人对罗马人憎恨的三个具体原因:罗马人“无耻的贪财”、对科林斯的洗劫、苏拉等晚期共和国将军的暴行。(24) 苏拉对支持米特里达提战争的希腊人的疯狂报复,无疑是自科林斯陷落以后希腊人再次蒙受巨大灾难的开始。公元前88年,小亚细亚希腊化的当地人王国本都的国王米特里达提六世发动反罗马战争,下令杀尽一切“罗马人”。虽然罗德斯岛等某些希腊城邦对罗马人提供了保护,但很多亚洲的希腊城邦以实际行动积极响应米特里达提的号召,对在东方的意大利人展开大屠杀。被杀者达8万或15万人之多。 甚至欧洲本土的希腊人也出于对罗马的仇恨而对米特里达提给予了广泛的支持。阿凯亚、拉哥尼亚、彼奥提亚和雅典等都成了米特里达提的同盟者。对米特里达提战争的支持,无疑是希腊人当中普遍蕴藏着的反罗马情绪的一次大爆发。这种反对情绪的直接根源在于罗马的剥削和干涉。
罗马的征服和剥削、米特里达提战争中的失败以及随后的罗马内战的摧残,实际上使希腊人在共和时期已变得意志消沉。在希腊化时代就已日益丧失其古典时代精神实质的城邦沦为罗马统治下的自治城市。虽然铭文资料显示希腊城市的政治活动依然频繁,但这些政治活动仅仅停留在罗马容许的范围,并且把持在安心于同罗马合作的贵族寡头手中。城市中虽然依旧存在对贪婪的罗马统治者的仇恨,但为了求得生存,这些城市不得不服从罗马统治者。城市之间的竞争也没有消失,而且在很多时候是对从罗马统治者那里获得某种特殊权利、地位或称号的竞争。当某个希腊城市向罗马统治者请求获得某种待遇或权利的时候,其派出的使节总是要讲述本城的光荣历史和有关传说、同罗马的友好关系和对罗马的贡献,以此作为支持他们这种请求的佐证,或是它应当受到与其他城市不同的特殊待遇或荣誉的理由。而罗马统治者关心的是整个罗马的事务,对某个希腊城市的政策往往只是从其现实的政治利益出发而定,于是该城市对罗马的贡献是被优先考虑的因素,而对希腊人讲述的光荣历史不感兴趣,或者鄙薄蔑视,甚至在必要时对该城市为罗马做出的贡献也不加理会。希腊城市有很长的崇拜希腊化统治者的传统,那么,无论是在共和时期还是在帝国时期,他们向罗马人提供类似的崇拜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帝国时期的希腊人也像整个帝国中的其他民族一样确立了对皇帝的崇拜。罗马人一方面鄙视希腊人的这种阿谀,另一方面又希望得到并愿意接受这种崇拜。希腊人虽然被迫对罗马人屈服和曲意逢迎,但同时怀有高度的文化优越感和自豪感,认为罗马人粗陋土气,缺乏文化精神,将他们归入蛮族之列。罗马人自己也清楚,希腊人对自己的鄙视丝毫不亚于自己对他们的鄙视。这些便是希腊人对罗马人的关系、态度以及在其中如何表达其民族认同的一般情形,这种情形从共和时代一直到帝国时代都没有根本性改变。(25)
对此,我们不妨看一下塔西陀记载的一个具体事例。公元23年,萨摩斯和科斯两个希腊城市派遣使团赴罗马,分别请求罗马确认前者的赫拉神庙和后者的阿斯克莱庇奥斯神庙的古老的避难权。“萨摩斯人的凭据是近邻同盟的一个决定,近邻同盟过去是一切事务的最高裁决机构,这个决定是在希腊人在亚细亚建立城市并统治沿海地区的时候作出的。科斯人陈述的古老根据也没什么两样,他们还加上了当地的一个功绩:因为当国王米特里达提下令在亚细亚的所有岛屿和城市中屠杀罗马公民的时候,他们曾让罗马公民进入阿斯克莱庇奥斯神庙避难。”(26) 德尔菲近邻同盟是一个在泛希腊范围内具有巨大影响的宗教同盟组织,那么,向罗马人述说其古老的权威性并请求对这种权威性加以重申,实际上也意味着希腊人在力图促成其民族的历史和认同传统获得罗马官方的承认。而科斯人强调救助过罗马人这条理由,显然是为了打动罗马人,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使自己古老的宗教传统能够更加顺利地获得承认。
在上述情况中,希腊人对文化和历史的进一步强调,实质上是对罗马这一“他者”的一种回应方式。不过,除了对待“他者”外,强调文化和历史的做法也出现在“自我”的公共空间内,即便这种空间因罗马统治的挤压而变得狭小了。例如,从公元前146年沦陷到公元前88年米特里达提战争爆发时为止, 希腊一直处在罗马强加的和平之下,除了城邦间某些边界纠纷外,再没有发生战争,和平中的希腊也让人看到了繁荣和宗教的复兴。考罗派的阿波罗(Apollon Koropaios)神谕所得到重建,其宗教事务得以恢复。雅典开始重新举行自公元前314 年停办的四年一度的提洛节(Delia)。公元前99年,罗德斯岛上的林多斯(Lindos)城编纂了自己的半神话半历史的宗教编年史,并将之铭刻于石碑之上。这就是学者所谓的《林多斯编年史》。(27) 这一时期的宗教复兴和编写乃至虚构自身光荣历史的举动,是一种在自我的公共空间内强化认同的行为。
公元前31年奥古斯都结束了罗马内战,此后便是帝国两个多世纪的“罗马和平”(Pax Romana),一直到公元267年黑鲁利人(Heruli)入侵时为止。 除了在马可·奥里略时期考斯托波奇人(Costoboci)入侵并被击退这一较小的动荡外, 希腊人再次生活在罗马强加的和平之下,而他们在以前的独立时代从未享受到如此长时间的和平。在大约公元50—250年之间即所谓的“第二智者时期”, 希腊人实现了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复兴。这一时期,雄辩术这种公共表演性演说成为最富有声誉的文学和文化活动,从事这种活动的演说家被称为“智者”(sophistes)。(28) 很多智者在其城市甚或行省中都颇有影响。他们常常通过自己的能力和声望来制止城市内部的骚乱或调停城市间的纠纷。他们还被派做使节前去为皇帝登基祝贺或者为本城市谋求某些特权。而且,大多数智者投入到教学活动中的时间和精力实际上要超过雄辩术,这就有力地推动了希腊教育的发展。“第二智者时期”不仅是公共演说繁荣的时代,在智者所发挥的文化主导作用之下,希腊人的其他各类文学体裁在此时都涌现了不朽的佳作。与此相联系的是整个希腊文化和经济获得了全面复兴,甚至城邦政治传统也在有限范围内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复苏。
智者演说使用的是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阿提卡方言, 演说中充满着对希腊伟大过去的旁征博引。语言形式及风格的复古和对往昔光荣的回顾也充斥于其他文学体裁中。这些智者、作家等知识分子大多数出身于富有的上层,并已成为罗马公民,有的甚至还享受到了皇帝赐予的某些特权,可以说是罗马政权下的受惠者,但其作品和言行不时流露出对希腊文化的更为自信,有时甚至不乏对罗马人近乎鄙视的述说,因而在希腊人当中颇受欢迎。而且,这种把目光更多地转向自身的历史和文化,以从中寻找和汲取引以自豪的民族精神力量的做法,并不只局限于上层知识分子,普通民众在这一点上反而比他们更为激进。在这种时候,作为罗马政权受惠者的希腊上层知识分子反而表现出了不安。普鲁塔克的一番言论很能反映这种情况:“各城邦的领袖荒唐地鼓动民众效仿祖先的功业、理想和行动,而这些在如今并不合时宜。他们本来很可笑,却未受到嘲笑,他们竟然根本没有受到鄙薄。”“马拉松战役、优里密顿河战役、普拉提亚战役以及所有会令民众躁动不安、恣肆妄为的事例都应该留给智者们讨论”,“不应激起风暴”。(29) 面对民众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为希腊文化自豪的上层知识分子的最终落脚点却是强调服从罗马的统治。他们往往在缅怀民族的光荣历史之后,忘不了提醒和告诫民众:这些光荣已不复存在,今天有更基本的任务等待着希腊人,那就是在和睦中生活,否则会招致罗马政府的干涉。(30)
三
公元前1 世纪的罗马诗人贺拉斯说:“被征服的希腊征服了其野蛮的征服者,将文艺带进了粗野的拉丁姆”。(31) 罗马对希腊文化的崇尚、吸收和提倡,不仅为其自身带来了收益,反过来也助长了希腊人的文化自豪感和优越感。某些当权者和皇帝实施的亲希腊主义政策对希腊人的民族认同也不无促进作用。
与罗马征服希腊人同步的是它大规模吸收希腊文化的过程。到公元前2世纪末,希腊语成为罗马人教育中的第一语言,受过教育的罗马人都是双语人。不过通常所谓的“罗马的希腊化”并非全盘的希腊化。公元前2世纪前期, 以加图为代表的传统派就曾对希腊文化进行了强烈的抵制。虽然这种抵制未能取得胜利,罗马希腊化的进程仍在继续,但罗马人最终走上的是一条选择性的希腊化道路,并在其“希腊化”中建构了自己强烈的罗马特性,而且还产生了欲与希腊人在文化上一争短长的嫉妒心态。罗马人也因此对希腊人加以贬斥,例如:认为希腊人性格“轻率”,而与罗马人的“沉稳”截然不同,“轻率”使他们的公民大会为反复无常的愚蠢暴民所操纵,使他们丢掉了独立并只知阿谀新主子;他们狡诈堕落,奴性十足而又傲慢自大,厚颜无耻;说话容易激动而过于草率,喜好卖弄理论,热衷于讲述神话;过分重视美术和音乐;他们在体育馆中的裸体锻炼对军事训练来说毫无用处。(32) 罗马人赋予希腊人一个囊括一切蔑视内容的小称词蔑称Graeculus(“小希腊儿”)。不过他们有时还把希腊人区别看待,例如将作为“文明”故乡的“古希腊”同“当代无精打采的希腊”对立起来,(33) 将“真正的希腊人”与希腊化东方的希腊人区分开来。(34) 当然,罗马人并没有忘记希腊人将他们也视为蛮族。
在对希腊人爱恨交加的复杂心态中,罗马人的亲希腊主义从共和时代到早期帝国时代呈现出不断增强的趋势。卢库卢斯(Lucullus)减轻苏拉强加给亚细亚行省希腊城市的罚金和税务,救助希腊难民返回自己城邦,从而受到希腊人的爱戴而被奉为“恩主”。希腊人还设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宗教节日。他喜爱希腊文化,其私人图书馆对希腊人开放。对于前来罗马的希腊人来说,他的家俨然成了“希腊人之家”。(35) 奥古斯都在阿克兴胜利后返还了安东尼攫取的某些希腊艺术品。他还将希腊哲学家留在宫中,并给予很高的荣誉。克劳狄授予很多希腊人以罗马公民权。尼禄在位时期,亲希腊主义政策出现了一次高潮。尼禄酷爱希腊的悲剧表演、歌唱和马车比赛。他不满足于在罗马召开和参加希腊样式的竞技会,还远赴希腊,花15个月的时间(公元66—67年)参加了所有泛希腊竞技会和重要的城邦竞技会。竞技会裁判也投其所好,全都宣布他为胜利者。他离开之前,在地峡竞技会会场上亲自宣布把自由授给整个阿凯亚行省。(36) 尼禄的亲希腊主义使他在希腊人中间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尼禄赋予希腊人的自由只维持了两三年的时间。“希腊人实际上并没有能够从这份赠予中得到好处,因为尼禄之后韦伯芗统治时期他们陷入了内部纷争,韦伯芗命令他们重新纳税和听命于总督,还说希腊人已经不懂得自由了。”(37) 到了图拉真时期,元老资格最终扩大到整个帝国的各个行省中。除开始被吸纳进元老院外,希腊人还在这时首次担任了执政官。(38) “第二智者时期”希腊文化的全面复兴中也不无罗马亲希腊主义政策的推动作用。
亲希腊主义到哈德良在位时期达到了最高峰。游遍帝国全境的哈德良更为青睐东部的希腊世界,对希腊人给以很多优待,比如在安条克兴修各种大型公共工程,充实亚历山大里亚的博物馆等。他尤其喜爱雅典,曾三访这座历史名城,并一向乐于给雅典和某些雅典人以好处。他们完成了雅典的“奥林波斯的宙斯”神庙的修建。他最辉煌的亲希腊主义举动,是应某些希腊城市的要求,在公元131—132年以雅典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全体希腊人的组织——“泛希腊同盟”。同盟的成员城市来自阿凯亚、色雷斯、亚细亚、克里特和库列涅等行省。他们派出被称作“泛希腊人”(Panhellenes)的代表组成议事会,议事会由执政官主持。 这些代表均为来自各行省的希腊显贵人士。即使学者对载有入盟资格的史料解读不一,但综合观之,入盟资格显然包括具有高贵的希腊特性和对罗马的忠诚。现存关于“泛希腊同盟”的史料主要是关于宗教活动的。同盟的中心崇拜是对艾琉昔斯的德墨特耳女神和被神化的同盟创建者“泛希腊的哈德良”(Hadrianus Panhellenios)的崇拜。同盟还建有“泛希腊的赫拉和宙斯”神庙和万神殿。史料也表明它不具有实质性的行政职能,很难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实体。“泛希腊同盟”至少持续至公元3世纪50年代,史料能够证实的最后一届“泛希腊节”即举办于此时。(39)
“泛希腊同盟”在一定程度上是哈德良亲希腊主义的政治产物,但其建立当中也包含着“力图将希腊人的民族感情引向文化和礼仪渠道”的意图,“它比喜好竞争而又招人讨厌的行省共同体更能有效地将这种民族感情置于帝国体制的束缚之下。”(40) 从希腊人方面而言,它也的确是其泛希腊主义的民族认同在罗马统治下的行动体现和实现形式之一。它提高了“老希腊”的声誉,促进了其传统和价值观在整个帝国东部希腊人世界中的复活和强化,确认了在罗马帝国统治境况下希腊人定义自身民族特性的取向。在对成员城市的选择中,它趋向于排除“边缘性”希腊化地区缺乏传统的城市,而乐于接受能够证明与“老希腊”有联系的城市。(41) 这实质上是以“老希腊”为标准来划定希腊民族共同体自身的族性边界,而历史和文化传统也就构成了希腊特性的核心内容和希腊人民族认同的主导动力。“泛希腊同盟”加强了帝国东部希腊城市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
罗马的亲希腊主义尽管有助于希腊人民族认同的强化,但同时也使希腊文化传统中某些要素的民族特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关于这一点,希腊竞技会为罗马时代的发展变化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事例。希腊人有着举办体育和文艺竞技会的悠久的宗教传统,众多大大小小的竞技会构成了不同圣所、地方、城邦和部落的宗教节日的组成部分。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早期,奥林匹亚竞技会、皮提亚竞技会(在德尔菲)、地峡竞技会和内美亚竞技会超出了一般的地方规模,发展为泛希腊竞技会。泛希腊竞技会的出现也是希腊人民族认同形成的标志之一。(42) 四大泛希腊竞技会因其奖品仅为简单的奖冠而被称为“奖冠竞技会”(stephanitai agones)。它们面向全体希腊人,并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只有希腊人才能够参加,而其参赛资格反过来也成了希腊人的一个身份认证。(43) 显然,泛希腊竞技会构成了希腊人的一种具有民族独特性的认同体制。
大约公元前300年以后,希腊人的竞技会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发展。 希腊化王国国王、希腊城邦和城邦同盟创建了很多新的竞技会。之后,罗马共和国晚期的动荡虽然使希腊的很多宗教节日和竞技会的举办一度陷入低谷,但随着帝国时代的来临,其原有的扩展势头又很快得到恢复,新创竞技会的风气延续了很长时间。罗马一些皇帝对希腊竞技会采取了扶持的政策,并且还亲自创设希腊式的竞技会。这样,在希腊化和罗马时代,泛希腊竞技会的数目也相应地不断增加。很多城市把它们重要的地方性竞技会提升成泛希腊竞技会,有的是像四大泛希腊竞技会一样的“奖冠竞技会”,有的则被宣布为“等同于奥林匹亚竞技会”(isolympia)或“等同于皮提亚竞技会”(isopythia)。 甚至在奥林匹亚和德尔菲以外的若干地方还新设立了很多名为“奥林匹亚竞技会”和“皮提亚竞技会”的竞技会。(44)
对于这些情形,似乎不可不谓之希腊竞技会的“繁荣”,但在罗马征服之后,这种“繁荣”也宣告了希腊人对于其泛希腊竞技会“专利权”的丧失。在希腊化时代,希腊化的非希腊人已经被认同为希腊人;他们只要证明自己的希腊属性,是能够参加泛希腊竞技会的。(45) 而到了罗马征服希腊以后,罗马人等外族人也被允许参加泛希腊竞技会,这样就打破了泛希腊竞技会不准非希腊人参加的惯例。(46)
由于罗马人对希腊竞技会在人员和政策上的介入,希腊竞技会的传统受到了一定的干扰和侵蚀,罗马文化的某些因素也逐渐渗透其中。例如,尼禄就曾下令把设在不同年份的竞技会集中在一年内举行,以至于有的竞技会重复召开,应于公元65年举办的第211届奥林匹亚竞技会则被推迟至公元67年。同样违反先例的是, 他还在奥林匹亚竞技会上举行音乐比赛。(47) 罗马时代很多新增的竞技会都与统治者个人崇拜或皇帝个人崇拜联系在一起,皇帝授权城市创建新的竞技会时还要考虑其政治忠诚情况。而更为严重的蜕变也在希腊竞技会身上悄然发生了,以前的希腊竞技会是对神祇和英雄虔敬的由衷表达,参赛者的目标是为个人、家族和城邦赢得荣誉;到了罗马帝国时代,希腊竞技会越来越向罗马式的公共“表演”靠拢,以吸引和取悦观众为主要取向,例如有些竞技会加入了角斗等罗马式项目,弥散着暴力和血腥。(48) 希腊竞技会在罗马时代的命运表明,对于希腊民族的文化传统来说,罗马人的亲希腊主义实际上有着推动和削弱的双重影响。
四
希腊人将整个人类区分为希腊人和蛮族人,意味着将罗马人也置于蛮族之列并将其推到了“文明”的对立面。尽管早在公元前1世纪末, 亲罗马的希腊历史学家哈利卡尔那索斯的狄奥尼修斯就曾试图证明罗马人在起源上也是希腊人,而且是比其他希腊部落“更古老和更加希腊的”(Hellenikoteron)希腊人,(40) 尽管普鲁塔克曾偶然将罗马人、希腊人和蛮族人三个名称并列,(50) 传统的希腊人—蛮族人两分法还是在长时期内被希腊人本能地保持着,即便在那些对罗马友好的希腊作家的著作中,甚至在“金嘴”狄翁对皇帝图拉真发表的“论王权”演说中也是如此。(51)
不过,像对其他被征服民族一样,帝国的权力和公民权对希腊人也产生了同样的吸引力。随着希腊精英与罗马政权合作的不断加深,以及获得罗马公民权的希腊人的逐渐增多,对罗马的认同也悄然而生。从现存的史料来看,罗马内战之前没有来自意大利之外的希腊人获得罗马公民权。内战过程中,苏拉、庞培、屋大维和安东尼等不同程度地将罗马公民权授予为自己服务的希腊上层或军官个人。元首制建立后,皇帝更为频繁地授予希腊人以罗马公民权。一些希腊人,主要是城市中的社会上层,也通过书面申请或他人举荐等方式从皇帝那里谋求官职或包括罗马公民权在内的民事权利。(52) 罗马公民权作为一种特权和荣誉,无疑有着表明和确认更高身份的意义,对罗马的认同也最容易体现在对罗马公民权颇为看重的心理上。至少在公元2世纪的史料中就已显露了这种端倪。 琉善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当一个没有文化、说话文理不通的希腊人夸耀罗马皇帝授予他罗马公民权时,犬儒学派的哲学家戴摩那克斯(Demonax)挖苦他说:“要是他使你成为一个希腊人而不是罗马人就好了。”(53) 这个故事也暗示了曾有过一个罗马认同与希腊认同并存和冲突的阶段。
从现存的文献来看,琉善是第一个将罗马帝国及其居民称为“我们”的希腊人。(54) 他称希腊历史学家阿里安为“第一流的罗马人”。(55) 稍后的埃利优斯·阿里斯提戴斯在对希腊文化和历史充满自豪的同时,又将罗马视为伟大的统一者,称之为“共同的城邦”、“一片绵延的国土”、“一个使一切民族臣服的民族”。他赞扬罗马人“使‘罗马’这个词不是一个城邦的名称了,而是成了一个共同的民族的名称;这个民族不是一切民族当中的一个民族,而是抵消了其他一切民族的民族”。他认为现在罗马已经把世界划分为罗马人和非罗马人,从而取代了原来希腊人和蛮族人的划分。(56)
公元212年,皇帝卡拉卡拉颁布《安东尼努斯敕令》(Constitutio Antoniniana),宣布将罗马公民权授予帝国境内全体自由民。对于该敕令,人们传统上常接受狄翁·卡西优斯的说法,(57) 认为其颁布动机可能是为了扩大继承税。A. N. 舍尔文—怀特认为,该继承税早已经存在,卡拉卡拉的动机是要扩展业已普遍的皇帝个人崇拜,把感召人们的统一观念完全落实,把“罗马人民的伟大”置于最可能的广泛认同基础之上。(58) 应该说,对于卡拉卡拉的这种意图,的确出现了某些积极回应的迹象:这之后埃及的大量纸草文献表明,那里的埃及人和希腊人虽仍保留着原有的传统,但敕令在最初已经带来了心理上和荣誉上的变化。(59) 这样,希腊人在保持自己民族传统认同的同时,开始普遍认同自己为罗马人。而且,两种认同还呈现出合流的趋势。例如,卡帕多奇亚主教格列高利·陶马图尔果斯(约公元213—217年)在赞美罗马法律的完善时说,“一言以蔽之,它是最为希腊的”。(60)
晚期罗马帝国东西部在发展上日益分道扬镳。公元330 年君士坦丁在拜占庭建立号称“新罗马”(Nova Roma)的新都(后改称“君士坦丁堡”),揭开了拜占庭帝国历史的序幕。罗马公民权被推广到整个帝国范围已使希腊语中“罗马人”(单数为Rhomaios,复数为Rhomaioi)一词被不加区别地用于帝国境内的各民族身上,而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化又使帝国和基督教世界合而为一,这样到公元4世纪末为止,“罗马人”变成了基督教徒的同义语。这也意味着“罗马人”一词丧失了民族内涵,而获得了政治和宗教的内涵,紧接着的连锁反应是“希腊人”(单数为Hellen,复数为Hellenes)这一名称民族内涵的丧失和宗教内涵的强化。在基督教的排挤下,希腊人日益放弃自己的传统宗教,转而信奉基督教。皈依基督教的希腊人只自称“罗马人”,而不再称自己为“希腊人”。“希腊人”则被用来指称那些仍旧固守古代希腊传统宗教的城市居民,他们通常是上层阶级。当城市基督教化后,该名称又被用于指任何一种多神教信奉者和偶像崇拜者,无论他是否说希腊语,乃至于最后该名称的使用被进一步推到了荒谬的极端:任何一种异教徒和蛮族人都被称为“希腊人”!(61)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实际上,“罗马人”取代“希腊人”作为希腊人自称的过程可能并非很快,某些偏远农村的希腊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还保留着旧称。而且,从公元7世纪以来, “希腊人”一词古代原有的民族涵义又在东正教之外的个别场合中复活了。“罗马人”虽是拜占庭时期希腊人通常的民族自称,但“希腊人”一词也偶尔被使用,有时使用中还带有民族自豪感。(62) 古代希腊民族文化的很多营养也被基督教所吸收,流淌在拜占庭时期希腊东正教民族文化的血液之中。拜占庭时期希腊人以“罗马人”和基督教徒身份为本位的民族认同并非对古代希腊人民族特性和认同的完全否定。
从一定意义上说,民族认同就是一个民族如何看待“自我—他者”的问题,如何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划分界限的问题。民族认同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被不断地建构和再建构着的;其建构常常是在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上进行的。
在希腊人传统的民族认同观念体系中,“希腊特性”和“蛮族人”分别构成了建构“自我”和“他者”的最基本的范畴。如何拿这些旧有的范畴去衡量新时代中的“自我”和“他者”,尤其是应对罗马这个非同寻常的新“他者”,如何在罗马统治的新环境下去重新界定和诠释这些旧范畴,便是罗马时代希腊人建构“自我”认同的内在逻辑。罗马人希腊化了,但却是有选择性地希腊化,故亦“非我族类”,也是“蛮族”。他们是希腊人的征服者,又是希腊文化的保护人,让人又恨又爱。在他们面前,自己无独立可言,却可大声言说独立时代先辈的荣光。在对往昔辉煌的重温之中,依旧能够体验作为“希伦子孙”的自豪,感受希腊语言的优美,表达对奥林波斯诸神的虔敬,享受迥异于“蛮族”的“文明”生活。而当自己也变成一个“罗马人”,而后又和罗马一起皈依了基督教时,却蓦然发现先前的“自我”竟是“蛮族”、“他者”了。这便是罗马时代的希腊人民族认同的心路历程。
事实上,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而言,罗马时代的希腊人所具有的认同不只一种,而是三种,即认同希腊、认同罗马、认同基督教。起初仅有希腊认同,属传统的民族认同。而后有了罗马认同,属国家认同,与希腊认同并存。基督教化后,罗马认同与基督教认同合一,兼有国家认同、宗教认同和民族认同三重性质,从而将希腊认同的民族认同性质排挤掉了。可见,真正断送了希腊民族认同的东西,并非仅仅是罗马帝国,而是罗马帝国和基督教的合谋,或者换句话说,并非仅仅是政治因素,而是政治因素和宗教因素的结合。宗教也是一种文化。基督教文化与希腊古典文化在精神实质上非此即彼,而古典的希腊文化作为“希腊特性”的综合体现,恰恰也是支撑希腊民族认同体系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古代希腊人的确是一支“文化民族”,靠文化认同,而终结其民族认同的,也是文化,是另一种文化。
注释:
① 关于这方面的论著很多,如马戎:《关于“民族”定义》,《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第5—13页;郝时远:《Ethnos(民族)和Ethnic group(族群)的早期含义与应用》,《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第1—10页;郝时远:《前苏联—俄罗斯民族学理论中的“民族”》,载王建娥、陈建樾等:《族际政治与现代民族国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6—182页;吉野耕作:《文化民族主义的社会学——现代日本自我认同意识的走向》,刘克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8—21页。
② M. I. Finley, “The Ancient Greeks and their Nation,”in M.I. Finley, The Use and Abuse of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Books Ltd., 1975, p. 123.
③ 徐晓旭:《古希腊人的“民族”概念》,《世界民族》2004年第2期,第35—40页。
④ 19世纪末20 世纪初,几位德国社会学家,尤其是弗里德里希·迈奈科(Friedrich Meinecke),将“民族”划分为“文化民族”(Kulturnation)和“国家民族”(Staatsnation)两种类型。这种理论分类虽然受到某些学者的质疑,但“文化民族”的概念适用于描述自身从未达到政治统一的古希腊人这一点却为一些学者所赞同。本文此处并非在严格的理论论证意义上,而是在具体描述意义上借用该词,目的是想以之突出“文化”在希腊人维系其民族认同中的意义。弗里德里希·迈奈科的有关论述见于Friedrich Meinecke: Weltbürgertum und Nationalstaat. Studien zur Genesis des deutschen Nationalstaats, München/Berlin: R. Oldenbourg, 1908, S. 7,转引自M. I. Finley, “The Ancient Greeks and their Nation,”in M. I. Finley, The Use and Abuse of History, pp. 123, 132; F. W. Walbank, “The Problem of Greek Nationality,”Phoenix 5, 1951, p. 44.
⑤ Herodotos, Historiai 8. 144. 2;所据希腊语原文的版本为Herodoti, Historiae, Editio tertia, Tomus posterior, recognovit breviqve adnotatione critica instrvxit C. Hude. Oxonii: e Typographeo Clarendoniano, 1927.本文其他各处引证的古典著作,除特别注明者外, 皆据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1—)中的希腊语和拉丁语原文。拉丁作家及其著作名称以拉丁语注明,希腊作家及其著作名称以希腊语的拉丁字母转写形式注明。引文的具体出处以国际学术界通用的卷、章、节等的标码标注。所有直接引用的引文均由笔者译成中文。此外,为减少希腊语和拉丁语繁琐的语法变化形式所带来的干扰和适应汉语的思维习惯,引证中夹注的某些希腊、拉丁名词在原文中的变格形式已被转换为主格形式,但其数的变化被保留。
⑥ 如E. Hall, Inventing the Barbarian: Greek Self-Definition through Traged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p. 6; H. Schwabl,“Das Bild der fremden Welt bei den frühen Griechen,”dans H. Schwabl et al., Grecs et Barbares, Genève: Fondation Hardt, 1961, pp. 1—36; H. Diller, “Die Hellenen-Barbaren Antithese im Zeitalter der Perserkriege,”dans H. Schwabl et al., Grecs et Barbares, pp. 39—68. 学者中还有另外两种关于希腊人—蛮族人两极对立观念出现时间的意见:《伊利亚特》成书(约公元前750年)之前;公元前8世纪到前6世纪晚期之间的某一时候。持前一种意见的著作如G. Murray, The Rise of the Greek Epic[4], Oxford and La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pp. 144—145.持后一种意见的著作如B. Snell, “Homer und die Entstehung des geschichtlichen Bewusstseins bei den Griechen,”in F.Klingner(Hg.),Varia variorum(Festschr.K.Reinhardt),Münster/Kln:Bhlau Verlag, 1952, S.7—8.两者均转引自E. Hall, Inventing the Barbarian: Greek Self- Definition through Tragedy,p.6.
⑦ 关于希腊人对于蛮族“他者”的建构问题,西方学者进行了很多探讨,可参见如下几例:P. Cartledge, The Greeks:A Portrait of Self and Others,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pp.36—62:chap.3“Alien Wisdom: Greeks v.Barbarians”;R. Browning,“Greeks and Others:From Antiquity to the Renaissance,”in Th. Harrison(ed.),Greeks and Barbarian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2,pp.257—277;W.Nippel,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ther’,”in Th. Harrison(ed.),Greeks and Barbarians, pp.278—310.
⑧ Isokrates, 4. Panegyrikos 50.
⑨ M. Hadas, Hellenistic Culture: Fusion and Diffusion,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pp.30—71.
⑩ M. I. Finley,“The Ancient Greeks and their Nation,”in M. I. Finley, The Use and Abuse of History, p.132;D.Noy,Foreigners at Rome, London: Duckworth with The Classical Press of Wales, 2000,pp.225,306—307.
(11) 以上四条铭文史料分别出自H. Wankel,Die Inschriften von Ephesos, Ia(IGSK,11,1),Bonn, 1979,24B; R. Meric et al.,Die Inschriften von Ephesos, Ⅶ,2 (IGSK,17,2),Bonn, 1981,3825;W.Ameling: Die Inschriften von Prusias ad Hypium(IGSK,27),Bonn, 1985, 3.均转引自Ed. Frézouls, “L'hellénisme dans l'épigraphie de l'Asie Mineure romaine,”dans S. Said(ed.),‘EΛΛΗΝΙΣΜΟΣ.Quelques jalons pour une histoire de l'identité grecque, Leiden, 1991,p.128.
(12) L.Moretti,Inscriptiones Graecae Urbis Romae, Roma, 1968—1990,1287,转引自D. Noy, Foreigners at Rome, pp.6,320.
(13) Kata Markon 7.26:he de gyne en Hellenis, Syrophoinikissa toi genei.所据希腊语原文的版本为A. Marshall and J. B. Philips(eds.),The Interlinear Greek-English New Testament, London:Samuel Bagster and Sons Limited,1958.
(14) Dionysios Halikarnasseus, Rhomaike arkhaiologia 1.89.4.
(15) Philostratos, Bioi sophiston 489.
(16) 人们普遍认为“金嘴”狄翁(Dion Khrysostomos)的第37篇演说《科林斯演说》(Korinthiakos)实际上是法沃里努斯的作品。此处所引内容见Dion Khrysostomos,37.Korinthiakos 25—27.
(17) F. Jacoby, Die Fragmente der griechischen Historiker, Berlin: Weidmann Verlag, 1929, S. 263,转引自A. N. Davies,“The Greek Notion of Dialect,”in Th. Harrison(ed.),Greeks and Barbarians, p.162.
(18) Ps. Hesiodos, Gynaikon katalogos, Eoiai, Fr. 9, Fr. 10(a).6—7, 20—24. 其中Fr.10(a).6—7,20—24系新近发现,转引自J. M. Hall, Ethnic Identity in Greek Antiqu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p.42.
(19) S. Swain, Hellenism and Empire: Language, Classicism, and Power in the Greek World AD 50—25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p.75.
(20) J. M. Hall, Hellenicity between Ethnicity and Culture,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pp.225—226.
(21) Tatianos, Pros Hellenas 1.1.
(22) E. S. Gruen, The Hellenistic World and the Coming of Rome,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p.356.
(23) A. Erskine, “Rome in the Greek World: The Significance of a Name,”in A. Powell(ed.),The Greek World,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pp.368—383;S. E. Alcock, Graecia Capta: the Landscapes of Roman Gree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pp.181—184.
(24) Oracula Sibyllina iii.189;iv.105;iii.470,转引自A. N. Sherwin-White, The Roman Citizenship,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0,p.400.
(25) A. Wardman, Rome's Debt to Greece, London: Bristol Classical Press, 1976, pp.33,36;J. P.V.D.Balsdon, Romans and Aliens,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9, p.30;P.Veyne, “L'identité grecque devant Rome et l'empereur,”Revue des études grecques 112(1999),pp.510—567.
(26) Tacitus, Annales 4.14.
(27) W. Tarn, Hellenistic Civilisation, London: Edward Arnold & Co.,1953,pp.39—40.
(28) 生活在该时期之末的智者兼传记作家菲洛斯特拉托斯(Philostratos)在其《智者传》(Bioi sophiston)中,认为该时期的智者同古典时代的智者之间存在联系。 他又将古典时代的“智者术”(sophistike)区分为“老智者术”(arkhaia sophistike)和“第二智者术”(deutera sophistike)。前者的特点是讨论大的哲学问题,后者是讨论历史发展中的具体问题。参见Philostratos,Bioi sophiston 481,484.现代学者便从菲洛斯特拉托斯那里借用了“第二智者术”一词,并将之略加变通地使用,创出“第二智者时期”这一名词。国内学术界通常将sophistike译作“诡辩术”,但这一译名因充满贬义而无法涵盖sophistike的全部所指,故弃而不用,代之以“智者术”这一具有中性语义的译名。
(29) Ploutarkhos, Politika parangelmata 17—19=Moralia 814A—815D.
(30) P. Veyne,“L'identité grecque devant Rome et l'empereur,”Revue des études grecques 112(1999),pp.510—567.
(31) Horatius, Epistulae 2.1.156.
(32) J. P.V. D. Balsdon, Romans and Aliens, pp.30—58, 161—163;E.Rawson,“The Romans,”in K. J. Dover(ed.),Perceptions of the Ancient Greeks, Oxford an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2, pp.1—28.
(33) Cicero, Epistulae ad Quintum fratrem 1. 5. 16;De Oratore 3.197; Tusculanae disputationes 2. 5.
(34) Cicero, Pro L. Flacco oratio 64—65; Plinius Junior, Epistulae 8. 24.
(35) Ploutarkhos, Lucullus 19.8,29.3—5, 42.1—3.
(36) Tacitus, Annales 14. 15, 20—21;Suetonius, Nero 21—25;Dion Kassios, Romaike historia 63.8—14.
(37) Pausanias, Hellados periegesis 7. 17.4.
(38) B. Levick,“Philhellene Emperors: The Interventions of Trajan,”in A. K. Bowman, P. Garnsey and D. Rathbone (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2[nd] ed., vol.Ⅺ,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pp.611—620.
(39) B. Levick,“Philhellene Emperors: Hadrian, Athens and the Panhellenion,”in A. K. Bowman, P. Garnsey and D. Rathbone(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2[nd] ed.,vol.Ⅺ,pp.620—627;A.J. S. Spawforth,“Attic Panhellenion,”S. Hornblower and A. Spawforth(eds.),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3[rd]. ed.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pp.1105—1106;S. E. Alcock, Graecia Capta:the Landscapes of Roman Greece,pp.163,166—168.
(40) B.Levick, “Philhellene Emperors: Hadrian, Athens and the Panhellenion”, in A. K. Bowman, P. Garnsey and D. Rathbone (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2[nd]ed.,vol.Ⅺ,p.625.
(41) S. E. Alcock, Graecia Capta: The Landscapes of Roman Greece, p.17;G. Salmeri,“Review: Olli Salomies(ed.),The Geek East in the Roman Context. Proceedings of a Colloquium Organised by the Finnish Institute at Athens, May 21 and 22, 1991. Papers and Monographs of the Finnish Institute at Athens, Ⅶ, Helsinki: Suomen Ateenan-Instituutin Sti,2001”,Bryn Mawr Classical Review 2002. 03. 17, . sas.upenn. edu/bmcr/2003/2003—03—17.html.
(42) C. Morgan, “The Origins of Pan-Hellenism,”in N. Marinatos and R. Hgg (eds.),Greek Sanctuaries: New Approach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p.18—44;S. B. Pomeroy, S. M. Burstein, W. Donlan and J. T. Roberts,Ancient Greece: A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78—79.
(43) 例如, 马其顿王室自称为希腊人的理由就是宣称其先祖亚历山大一世曾参加过奥林匹亚竞技会。而在这一传说中,亚历山大一世最初的参赛要求也被希腊人拒绝,只有当他证明自己血统来自希腊城邦阿哥斯后,才被判定为希腊人而被允许参加比赛。见Herodotos, Historiai 5.22.
(44) S. J. Instone and A. J. S. Spawforth,“Agones,”in S. Hornblower and A. Spawforth (eds.),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3[rd] ed.,pp.41—42;D. C. Young, A Brief History of the Olympic Games, Malden, Oxford and Victoria: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 pp.130—134;J. Fontenrose,“The Cult of Apollo and the Games at Delphi,” in W. J. Raschke (ed.),The Archaeology of the Olympics: The Olympics and Other Festivals in Antiquity,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8,pp.121—139.
(45) 例如,西顿是个希腊化的腓尼基城市, 一则铭文中提到一个西顿人曾参加过奥林匹亚竞技会,还有一则铭文中也提到一个西顿人曾参加过内美亚竞技会,两则铭文里又都利用希腊神话来证明和强调西顿与希腊的联系。参见R. J. van der Spek,“The Babylonian City,”in Amélie Kuhrt and Susan SherwinWhite(eds.), Hellenism in the East:The Interaction of Greek and non-Greek Civilizations from Syria to Central Asia after Alexander, London: Gerald Duckworth & Co.Ltd., 1987,p.59;S.Price, Religions of the Ancient Greek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p.8.
(46) 特拉雷斯的弗莱工(Phlegon Trallianos)所撰的《奥林匹亚竞技会胜利者名录和编年史集》(Olympionikon kai khronikon synagoge)中提到的第一个在奥林匹亚竞技会上获胜的罗马人叫盖优斯(Gaius),他在公元前72年召开的第177届奥林匹亚竞技会上取得了长跑项目的冠军。弗莱工的这部著作全书已佚,上述内容保留在佛提奥斯(Photios)编纂的《书库》(Bibliotheke,或称《万卷书》,Myriobiblon)中,见Photios, Bibliotheke 97 p. 83[b];据. org/fathers/photius_03bibliotheca. htm #97所载J. H. Freese的英译文。
(47) Suetonius, Nero 23. 1; Philostratos, Ta es ton Tyanea Apollonion 7.192.
(48) K. J. Gallis,“The Games in Ancient Larisa: An Example of Provincial Olympic Games,”in W. J. Raschke(ed.), The Archaeology of the Olympics: The Olympics and Other Festivals in Antiquity, pp. 217—235;D. P. Harmon,“The Religious Significance of Games in the Roman age,”in W. J. Raschke (ed.), The Archaeology of the Olympics: The Olympics and Other Festivals in Antiquity, pp. 236—255.
(49) Dionysios Halikarnasseus, Rhomaike arkhaiologia 1. 5, 89.
(50) Ploutarkhos, Perites Romaion tykhes 11=Moralia 324 B.
(51] Dion Khrysostomos, Peri basileias Ⅰ14; Peri basileias Ⅳ 25.
(52) A. N. Sherwin-White, The Roman Citizenship, pp. 246—250, 294—299, 306—311.
(53) Loukianos, Demonaktos bios 40.
(54) Loukianos, Pos dei historian syngraphein 5, 17, 29; Alexandros e pseudomantis 48.
(55) Loukianos, Alexandros e pseudomantis 2.
(56) Ailios Aristeides, Eis Rhomen 26, 30, 63—64,转引自A. N. Sherwin-White, The Roman Citizenship, pp. 426—428; R. Browning,“Greeks and Others: from Antiquity to the Renaissance,”in R. Browning, History, Language and Literacy in the Byzantine World, Northampton: Variorum Reprints, 1989, chap.Ⅱ, pp. 10—11.
(57) Dion Kassios, Romaike historia 78. 9. 5.
(58) A. N. Sherwin-White, The Roman Citizenship, pp. 277—287.
(59) M. Le Glay, J. Voisin, Y. Le Bohec and D. Cherry, A History of Rome, trans. A. Nevill,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1, p. 358.
(60) Gregorios Thaumatourgos, Ad Origenem I, PG 10. 1053 A,转引自 R. Browning,“Greeks and Others: from Antiquity to the Renaissance,”in R. Browning, History, Language and Literacy in the Byzantine World, chap.Ⅱ, p.11.
(61) A. Garzya,“Byzantium,”in K. J. Dover(ed.),Perceptions of the Ancient Greeks,pp.29—53;P.Brown, Power and Persuasion in Late Antiquity: Towards a Christian Empire,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2,pp.129—133.例如,将军弗拉维图斯(Fravittus)被反基督教的异教作家佐西摩斯(Zosimos)称赞为“虽然在种族(genos)上是个蛮族人,但是在其他方面,不仅在生活方式(tropos)上,而且在精神风貌(proairesis)和对神事的虔敬(he peri ta theia threskeia)上都是个希腊人。”见Zosimos, Nea historia 5. 20. 1,转引自A. N. Sherwin-White, The Roman Citizenship,p.458.
(62) A. Garzya,“Byzantium,”in K. J. Dover(ed.), Perceptions of the Ancient Greeks, pp. 29—53.
转自《历史研究》(京)2006年4期第148~163页
责任编辑:刘悦
分享到: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
最新更新
猜你喜欢
关注我们


 当代时讯
当代时讯  中国历史
中国历史  世界历史
世界历史 历史典故
历史典故  历史百科
历史百科  野史秘闻
野史秘闻  民间故事
民间故事  神话传说
神话传说  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  网站首页
网站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