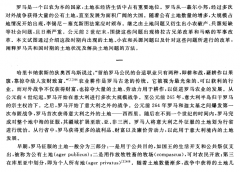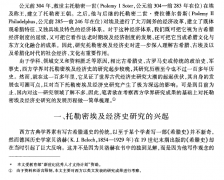托勒密埃及的法律与司法实践
作者简介:
郭子林
【英文标题】Law and Judicial Practice of Ptolemaic Egypt
【作者简介】郭子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06
【内容提要】 受法老埃及法律和希腊及近东其他地区法律的影响,托勒密埃及分别实行适用于当地埃及人和外来移民的法律体系。两种法律体系很少发生冲突,但一旦出现两者都无法解决的问题或危及国王和统治阶级利益的情况时,国王便以仲裁者的身份,以赦令或敕令的方式颁布针对具体问题的法律,从而使两种法律体系处于事实上的和谐状态。无论是托勒密埃及的司法机构,还是司法诉讼和司法审判,都体现了这一特点。这一法律及司法体系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弱者的利益,惩治了作恶者,保持了社会的稳定。然而,托勒密埃及的法律始终受到国王的控制,是国王个人意志的体现。
【关 键 词】托勒密埃及/法律/司法/专制王权
托勒密埃及(前323—前30年)的法律与司法实践是揭示身处法老埃及①与罗马统治时期埃及之间的社会政治史的重要面相。从法学的角度讲,研究该问题有助于澄清法老埃及的法律在托勒密埃及的延续情况,甚至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古代法律的特点。从历史学的角度讲,该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分析托勒密国王②如何处理希腊传统法律与埃及传统法律之间的冲突,以及如何利用法律来加强统治,从而使我们进一步理解托勒密埃及专制主义的特点。然而,由于史料的缺乏,国外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仍处于一般性探讨阶段,大多论述托勒密埃及历史和具体问题的著述只是对法律略作介绍,或者有些研究古代埃及法律的文章仅仅把托勒密埃及的法律作为文章的一个部分而简单叙述,专门研究这种法律的论文和著作并不多见。
最值得一提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古代文明史教授兼波兰克拉科夫大学罗马法教授道本史莱格所著《公元前332年至公元640年希腊罗马埃及纸草文献中的法律》一书。该书通过解读纸草文献中记载的法律内容,较为系统地研究了希腊罗马统治时期埃及的法律,讨论了希腊传统法律、埃及传统法律、罗马法律在该时期司法实践中的关系,并分别叙述了私法、刑法、司法程序和执行、政治法、管理法、管理程序和执行等,认为“埃及法律与希腊法律在希腊人统治时期的埃及相互影响,在罗马时期形成统一法律”。③此著作没有专门考察托勒密埃及的法律,而是把其纳入较长时段的历史中研究,不利于突出该时期法律的特殊性;而且此书主要从法学的角度出发,侧重于探讨纸草文献展现的法律内容本身,忽略了希腊罗马统治时期埃及的历史背景,忽视了这种法律在形成条件、内容以及司法实践等方面体现的独特性,更没有深入分析这种独特性的深层次原因。
我国尚无专文论述托勒密埃及的法律。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界对托勒密埃及法律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很多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例如,托勒密埃及法律的渊源、体系和内容、实施法律的司法机构、司法机构的演变过程、这种法律及司法实践的特点等等。本文试图根据考古学和历史学提供的史料对这些问题进行历史学的分析和解答,进而揭示托勒密埃及法律及其司法实践所体现的特点。
一、托勒密埃及法律的渊源
公元前323年,托勒密一世出任埃及总督之时,埃及的人口构成已经相当复杂,不仅有作为统治者的马其顿人和希腊城邦移民④及其联盟——西亚各地移民⑤和犹太人,还有作为被统治者的当地埃及人。⑥这些在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人们是否有各自的法律?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他们各自的法律或者法律传统是怎样的?
古代西亚移民和犹太人显然具有悠久的法律传统。两河流域的古代国家不仅有法律,还很早就颁布了法典,如《乌尔纳木法典》、《李必特—伊丝达法典》、《埃什努那法典》和《汉谟拉比法典》等。⑦对于犹太人来说,《旧约圣经》也是一部法律汇编,尤其《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构成了《旧约圣经》的第一部分——《律法书》,其中《出埃及记》(20:3-17)和《申命记》(5:7-21)中的“十诫”更具法律效力。
古代希腊并不像罗马那样有法典流传下来,但近年国外很多学者坚持认为古代希腊有法律。希腊的法律源头可追溯到公元前1200年的荷马时代,下限可至公元前30年罗马征服埃及时期。⑧希腊法律当中,雅典法律最具代表性。雅典最早的立法者是德拉古,接下来是梭伦、克里斯提尼、伯里克利、德莫斯提尼等。他们通过的一系列改革条例,在实践中变成了雅典的法律。⑨在这一过程中,雅典形成了一系列体现民主精神的法律制度、审判制度和程序以及法律传统等,成为希腊世界法律的代表。⑩其他希腊城邦(包括马其顿)的法律不太明确,但这些城邦或国家在与雅典的长期交往中,必然受到雅典法律的影响。正如卡里和哈阿霍夫认为的那样,至少“到公元前600年,希腊人运用的法律变得足够复杂,被明晰地编成法典,城市之间竞相编纂和出版自己的法律书”。(11)
埃及是否有法律?这是埃及学专家一直讨论的问题。一些人认为埃及没有法律,(12)也有人认为埃及有法律。(13)但近些年学者们大多倾向于后一种观点。(14)古代埃及象形文字“hp”一词最初出现于中王国(约前2000年),在圣书体和祭司体文献中,通常被译成“法律”;而后来在世俗体文献中,这个词的意思因语境不同可翻译为“法律”、“习俗”、“法规”、“权力”、“正义”等,其涵义有所扩大,但其主要意思仍是“法律”和“法规”。(15)在现有的文献中,有时可以看到“写下来的法律”、“国王的法律”、 “国家的法律”、“监狱的法律”等等。(16)古典作家希罗多德(前484—前330/320年)在其著作中记载了一条关于古代埃及奴隶可以到神庙寻求庇护的法律。(17)生活于“希腊化”时代末期的狄奥多拉斯记载了古代埃及的许多法律现象,例如对伪誓者、诬告、杀人、逃兵、泄密等进行惩罚的法律,还有关于契约、盗贼、婚俗和葬俗等的法律。(18)从文字、文献记载以及古典作家的记述来看,法老埃及确实存在法律法规。但是,法老埃及的法律不像古代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那样以正规的法律条款的形式存在,而主要是以国王敕令的形式出现。在法老埃及,国王的话和敕令就是法律。(19)在长期实践中,法老埃及形成了很多惯例,这些惯例也是埃及传统法律的一部分。(20)在一定程度上讲,法老埃及法律中的相当大一部分内容属于习惯法或习俗法。(21)
当然,法老埃及的法律也经历了一个形成演变的过程。法老埃及法律最初与宗教密不可分。费尔施迪克指出:“对于古代埃及人来说,玛阿特(Maat)观念是法律的首要原则。”(22)德国图宾根大学的莎菲克·阿拉姆教授一直从事法老埃及法律的研究,他通过对西底比斯地区戴尔·埃尔—美迪纳工人村出土的档案文献的研究,发现埃及的法律与宗教有着内在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讲,在古王国时期(前2686—前2181年),随着专制主义统治的确立,埃及的法律从宗教中分离出来,并且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民法与刑法之别;在司法审判结束之后,法庭还要执行审判结果,并不像传统观点认为的那样,埃及法庭只是在庭审结束时简单宣布“A方是正确的,B方是错误的”,而不执行审判结果。(23)之后,埃及的法律逐渐完善起来,尤其到法老埃及后期(Later Egypt)(前1085—前323年),已经形成了各种实体法,如关于财产、家庭、继承、犯罪、契约、商业以及贸易、个人地位等方面的法律。(24)
法老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敕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作一种立法活动。据狄奥多拉斯记载,古埃及的立法活动始于第一王朝的建立者美尼斯。(25)实际上,美尼斯很可能并非第一王朝的建立者。(26)不仅没有任何考古证据证明美尼斯曾进行立法活动,事实上连美尼斯是否为真实的历史人物都值得怀疑。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认为,阿苏启斯统治时期,“埃及财政困难,因此定出一条法律,一个人可以用他自己父亲的尸体作抵押来借钱;法律还规定,债主对于债务人的全部墓地拥有财产扣押权,如果债务人还不了债,对于提供这种抵押的人的惩罚就是,他死时不许埋入祖坟或其他任何墓地。”(27)阿苏启斯是第四王朝(前2613—前2498年)继承了孟考拉王位的舍普塞斯卡夫。希罗多德的这处记载是否真实还无从考证。从考古证据来看,第五王朝《尼斐利尔卡拉王的阿拜多斯敕令》(Edict of King Neferirkare at Abydos)的内容是针对具体问题做出的一些具有约束力的规定,这是迄今所知法老埃及最古老的一份法律文献。(28)
新王国时期的两份铭文进一步为我们提供了古代埃及人进行立法活动的考古学证据。一份文献是在第十八王朝法老图特摩斯三世(前15世纪中期)的维西尔(29)莱克米尔(Rekhmire)的墓中发现的,文献中有这样一句话:“40卷Shezemu(sm)在他面前”。“Shezemu”意为“皮革”,即羊皮纸卷。有人认为这40卷羊皮纸卷是成文法典,因为维西尔担有法官的职责。(30)狄奥多拉斯认为这是由8个部分组成的成文法典。(31)如果这种说法被证实的话,那么古代埃及早在公元前15世纪中叶就已经有了成文法典,因而必然有了明确的立法活动。但是,这种推断存在很多疑点。首先,维西尔相当于中国古代的宰相,他的一个重要职责是管理财政,而埃及的财政报表数量很大,这40卷羊皮纸卷也有可能是财政报表。其次,维西尔还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面前的这些东西也许是某种权力的标志,比如某种象征权力的鞭子。再者,如果这些的确是成文法典的话,数目如此庞大的法典一定会引起当时埃及人的注意,会在铭文与文献中留下某些蛛丝马迹,但遗憾的是,除了铭文上的这句话,目前没有任何其他证据可以佐证这些羊皮纸卷是法典。这份文献如果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另一份文献则完全可以证实埃及人有过明确的立法活动。这份文献是第十八王朝法老郝列姆赫布颁发的敕令(大约公元前14世纪中期),刻于卡尔纳克的郝列姆赫布墓的墓碑上,其内容是对王室必需品的贡纳和税收中滥用权力者的惩罚条例。该敕令得到了同时期其他文献的佐证。这份铭文使我们确信,最迟到公元前14世纪中期埃及已经有了明确的立法活动。(32)
法老埃及是否已经有了法典?这也是学界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凯姆普等人认为,埃及在古王国时期,或者最晚到中王国时期可能就存在法典了。(33)提奥多里泰斯认为“尼罗河谷没有制定出法典”。(34)我们更倾向于认为法老埃及历史后期出现了法典。狄奥多拉斯记载,法老埃及后期有三位著名的立法者:伯克霍利斯、阿玛西斯和大流士一世。(35)大多数现代历史学家认为大流士一世曾在埃及编纂过法典,因为大流士是波斯国王,来自古代西亚,而西亚又有编纂法典的传统。据说,大流士对他的前辈冈比西斯在对待埃及神庙上表现出来的目无法纪心怀不满,渴望过上一种对神祇虔诚和道德的生活。大流士征服了埃及以后,“与埃及祭司建立了密切关系,并且亲自参考了有关圣书中记载的事件和理论思想的研究成果。他从这些书中了解到国王的伟大和善待臣民的态度,还模仿了这种生活方式。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是所有国王(外来国王)中唯一一位在活着的时候就被奉为神灵的人物。在他死后,根据埃及传统,人们给予他与古代埃及国王平等的荣誉。”(36)另一种说法是:在大流士统治的第3年(前519),他命令埃及总督建立一个由战士、祭司和书吏中的贤能之士组成的委员会,记录直到阿玛西斯统治第44年的埃及法律。阿玛西斯只统治了44年(前570—前526),所以大流士的目的是制定一部直到波斯征服时期的埃及法律。这个委员会工作了16年,所著法律文献以双语版本出现:亚述语版本和埃及世俗语版本。(37)
大流士法典是否流传到了托勒密埃及时期?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得求助考古成果。1938年10月,考古学家们在盖尔伯(赫尔摩坡里斯西部地区)发现了一份世俗语纸草文献,30年以后发表出来。这篇文献可能是在公元前3世纪完成,大约是托勒密二世统治时期(前282—前246年)。文献包含了200多个案例,主要涉及民事争端。文献的作者把这些案例分成了四类:涉及土地租赁问题的案例,涉及继承问题的案例,涉及邻里争端的案例以及关于其他问题的案例。德国图宾根大学埃及学研究所的莎菲克·阿拉姆教授认为,这份文献可能是托勒密王朝初期的一个法官编纂而成的,其中的案例可能来自法老埃及的不同时期。(38)比利时学者卡格贝尔认为,这份文献是埃及神庙祭司为满足他们的各种实践需要而编纂的包括宗教、科学和司法审判等内容的手册。从司法的角度,可以将其称为“祭司用的埃及法律案例书”(简称“案例书”)。此案例书为托勒密埃及的法官们提供了某些法律依据。1931年,考古学家们在塔布突尼斯也发现了一份世俗语纸草文献,50年后由布列西阿尼发表。尽管这份文献的内容残缺不全,却是世俗语祭司案例书的另一个副本,其版本形式与上述赫尔摩坡里斯文献相差无几。最近,有一些公元前100—前50年的孟菲斯纸草残篇也陆续发表出来。(39)可见,各种版本的案例书在托勒密埃及出现并在实践中使用。这些案例书是由埃及祭司收集并保存于神庙中的档案材料,大流士法典编纂委员会有埃及最好的祭司参加,他们一定会利用神庙的档案材料,而案例书恰恰取自神庙档案材料。也就是说,这些案例书与大流士法典有着相同的来源,因此这些案例书即便不是大流士法典的一部分,也与大流士法典有着不可或缺的联系。这样,我们可以认为,法老埃及不仅有法律,而且最晚到公元前6世纪末还有了法典,立法者是法老。古代埃及的法律被埃及祭司以收集案例书的方式保留了下来,并且流传到托勒密王朝统治时期,为托勒密王朝统治当地埃及人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托勒密埃及的法律体系及其内容
希腊移民、西亚移民、犹太人和埃及本土人都有一套传统法律,而且这些法律既不统一,也不易融合,因此托勒密埃及实行了分别适用于当地埃及人和外来移民的两套法律,即埃及当地法律和所谓的“城市法”。
埃及当地法律又称“除希腊城市之外的埃及地区法律”(nomoi tēs choras),是法老埃及流传下来的法律,是一种习惯法,存在于各种敕令、“案例书”或者祭司神庙档案中。托勒密王朝的各种“案例书”是祭司们在执行专业性活动(如订立契约)和审判时可以依据的重要材料。托勒密王朝把这些案例书翻译成了希腊文,从而案例书也被提高到了官方法律的地位。(40)
外来移民在托勒密埃及遵守的是所谓的“城市法”(politikoi nomoi)。埃及当地人可以遵守他们自己的传统法律,但作为征服者的希腊人没有任何可以共同遵守的成文法典,希腊各城邦都曾保持和发展各自的习惯法。托勒密埃及的统治者也允许希腊移民继续遵守他们的习惯法。但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来自各个城邦的希腊移民逐渐达成共识,法律意识逐渐协调一致,各自法律的不同渐渐消失,最终采用了所谓的“希腊化共通法”。(41)
在托勒密埃及的希腊城市居住着许多犹太人,作为外来移民的一部分,他们也遵从希腊城市法,但他们也有自己的法律传统。考虑到犹太人对自己传统法律和风俗的忠诚,托勒密王朝把犹太人的法律翻译成了希腊文,作为城市法的一部分。《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是公元前3世纪由希伯来文的《托拉》(尤其是第一部分《摩西五经》)翻译成希腊文的,大约在托勒密二世时期完成。这是因为埃及的犹太人已经是托勒密王朝的臣民了,这些经文变成了“埃及的犹太人城市法”,作为与希腊城市法地位相同的法律法规,在司法实践中起到了实际作用。(42)犹太人既要遵从希腊移民的希腊化共通法,还要遵从自己的犹太人城市法。居住在犹太区的希腊移民也要遵从犹太人的城市法。由此可见,托勒密埃及的“城市法”由两部分构成:“希腊化共通法”和“埃及的犹太人城市法”。
托勒密埃及的法律基本上是以这样一些形式存在:案例书、《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国王敕令、契约以及各种习惯法。(43)我们发现了很多以契约形式存在的法律文献。比如,公元前250年,一个农民为了保释一位囚犯,与国王签订了契约。契约规定保释者必须定期把被保释者带到国王的代理人面前,如果保释者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他就会付出一定的代价,并且他的“所有财产,现在和以后所有的,都作为执行此义务的保证”。(44)这份契约具有法律效力,对契约当事人有约束力。
托勒密埃及的法律涉及方方面面的内容:行政方面的法律,例如国王颁布的对官员任命、惩罚等的敕令;经济方面的法律,例如有关税收和出口贸易等的法令、关于制订契约的惯例;外交方面的法律,如关于和与战问题、有关与邻国联姻问题等的法令;宗教方面的法律,例如关于崇拜神祇和建筑庙宇等的政令;社会生活方面的法律,例如婚姻法、遗嘱、继承法等。(45)公元前3世纪中期,一部亚历山大城城市法引人注目,这份法律文件是以希腊文写成的,只保存下来几个条款,这几个条款涉及人身攻击的处罚问题,都规定了明确的责权利关系,并有具体的量刑标准和惩罚措施。比如,“如果男奴隶或女奴隶攻击了男性自由人或女性自由人,那么奴隶将被鞭笞不少于100下;或者如果他们的主人承认事实,那么主人将代替他(她)支付受到攻击的自由人所提出的罚款额的2倍罚金。如果奴隶否认事实,原告可以控告他(她),那么他(她)将被处以3倍罚金;对于较为严重的攻击,原告在提起诉讼时应对伤害行为做出评估,无论法庭确定的罚金是多少,奴隶的主人应该缴纳3倍的罚金”。(46)
托勒密埃及的法律从体系上看是两种法律并行发展,从内容上看是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我们从托勒密埃及的法律文献中很少看到两种法律相冲突的情况,只存在两种法律体系中的一种或两种都无法解决某一问题的情况,或者出现危及国王和统治阶级利益的情况。此时国王便以协调者或仲裁者的身份出现,以敕令或者赦令的方式颁布针对具体问题的法律,这样便使两种独立发展的法律处于一种事实上的和谐状态,其法律体系呈现出明显的“二元性”特征。例如,公元前259年,托勒密二世为了对植物油的制作与出售等进行专营并结束之前植物油生产与经营的混乱状态,颁布了一道敕令,对植物油生产、加工、出售等具体环节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重新规范,并作为相关问题的法律依据。(47)公元前118年,托勒密八世和他的两位妻子共同颁布的一道赦令,便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法律上的重新规范,使社会暂时恢复了往日的“宁静”。(48)
当然,从保存下来的档案文献以及托勒密埃及的法律体系及其内容等来看,托勒密埃及的法律仍然是习惯法。虽然有一些案例书和可供参考的敕令,但在司法实践中,人们仍主要以传统和习惯为基础,以传统和惯例为标准,并根据具体情况,适时地对法律做出有利于统治阶级利益的修改,甚至重新立法。总之,托勒密埃及还没有形成一部可以基本上平衡各种利益关系、以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宗旨、长期有效的法律文书。
三、托勒密埃及的司法机构
法律是整个司法活动的基础和依据,反过来,司法机构和司法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体现法律的特点。托勒密埃及的司法机构自始至终也不是单一法庭,而且法庭构成也不是恒久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形势和社会复杂程度的变化而变化,其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公元前4世纪末期到前3世纪早期,在托勒密埃及经济活动当中,人们的债务契约基本用两种语言(希腊语和埃及语)写成。一份契约分两部分,两部分的内容一致,上半部分被折起,并加盖印章,有证人在场。下面的部分可以看到。如有改动,打开上半部分就知道最初的内容。最初,契约存放在一个地位较高的某个人那里。后来,私人之间的契约要到一个被称为阿格诺米亚(agoranomeia)的档案处登记,从而可以保证借贷的安全。阿格诺米亚是由许多阿格诺莫(agoranomo)(证人)组成的委员会。婚姻财产公证和土地买卖契约体现了这个委员会的存在价值。(49)这个委员会或许在托勒密一世统治时期起到了重要作用,甚至起到了法庭的作用。但托勒密一世统治时期,埃及是否有其他法庭,仍是个谜。阿格诺米亚一直存续下来,“到公元前2世纪,委员们除了登记契约,还要把契约的世俗语内容翻译成希腊语,从而导致工作量增加,这样埃及书吏数量也随之增加。”(50)最终,这个委员会的地位大大降低,仅相当于档案馆。可以说,地位较高的个人和阿格诺米亚是托勒密埃及最早的法官和法庭,但其具体运作过程仍不为人知。因为史料不足,所以这个阶段的法庭情况基本上是模糊不清的。
公元前275年,托勒密二世在全国设立两种法庭:“克莱美提斯泰法庭”和“劳克瑞泰法庭”。这是托勒密埃及法庭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前者是设在埃及全境各地的“希腊法庭”,由希腊马其顿移民任法官,称为“国王审判官”,由首席司法大臣任命;后者是设在希腊城市之外的埃及境内的“埃及法庭”,由土著埃及祭司担任法官,称为“王室法官”。这两个法庭是根据族群标准设立的。希腊法庭处理希腊人之间的纠纷,埃及法庭处理埃及人之间的纠纷。当埃及人与希腊人之间发生纠纷时,在另一个专门的法庭处理,即“考伊诺狄钦法庭”,或称“混合法庭”,由希腊人和埃及祭司联合充任法官,这个法庭只存在于公元前3世纪,后来就消失了。(51)如果埃及人之间的法律诉讼不是在埃及法庭解决,而是在希腊法庭或其他根本不懂埃及语的官员那里解决,那么这时绝不会用希腊人的法律来随意处理,而是借助被翻译成希腊语的埃及法律来处理。(52)这样的法庭设置是与公元前3世纪的社会状况相适应的。但是,随着埃及人与希腊人之间的接触和往来越来越频繁,相互之间的纠纷也越来越多,而且多与经济诉讼有关,最终这种简单地以族群身份作为选择法庭类别的标准的做法便不合时宜了。
公元前2世纪,托勒密埃及的法庭得到进一步发展。公元前118年,托勒密八世和他的两个妻子克娄巴特拉二世、克娄巴特拉三世,联合发布了一份结束内战的赦令,赦令中的一个条款规定:“用希腊语与希腊移民订立契约的埃及人,应在希腊法庭提交诉讼,并获得满意解决。埃及人与埃及人之间的诉讼,不应由希腊法庭处理,而应在埃及法庭根据国家法律裁决”。(53)这一赦令条款为托勒密埃及法律诉讼机构的选择提出了双重标准,既坚持原有的族群标准,又可以根据诉讼中涉及的契约的语言来选择法庭。也就是说,埃及人与埃及人、希腊移民与希腊移民之间的纠纷还按原来的族群标准选择法庭;而埃及人与希腊移民之间的纠纷则根据所涉及契约的语言来选择法庭,如果契约是埃及语的,那么则在埃及法庭解决诉讼,如果契约是希腊语的,则在希腊法庭解决诉讼。
如果希腊移民与埃及人之间的纠纷没有涉及契约问题,那么这种纠纷在哪个法庭处理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公元前2世纪时,托勒密埃及还设立了一个专门的法庭——“十人委员会”,由希腊人和埃及人共同担任法官,处理埃及人与希腊人之间不涉及契约问题的纠纷。(54)
“耕种王室土地的人、政府垄断部门的工人、其他那些与税收有关的人”的诉讼,涉及王室地产、某些官员、王室佃农等,关系重大,往往由国王或者首席司法大臣直接处理或由希腊法庭的法官处理。另外,宫廷内部的各种纠纷和案件,一般都由国王委派的各种行政官员来审理。(55)公元前2世纪,地方官员有时也兼具法官之职能,如地方总督等。(56)这种法庭制度一直延续到公元前30年托勒密王朝灭亡。
无论法庭的设立与沿革,还是法官以及其他行使法官职能的官员的司法活动,都体现了法律的决定作用。正是托勒密埃及法律的“二元性”特点决定了法庭和官员的“二元性”,两种机构和法官并行存在,同时起作用。遇到两个法庭都解决不了的情况,则由协调机构(即国王或官员或混合法庭)来处理,从而基本达成法律实施机构的和谐共存。另外,国王、非法官身份的官僚可以行使法官职能这一史实表明,托勒密埃及的司法体系还未制度化。
四、托勒密埃及的司法诉讼
托勒密埃及法律赋予了司法诉讼以特殊的形式和内容。托勒密埃及的主要诉讼形式是请愿。(57)托勒密埃及为我们保留了很多请愿文书,包括向国王和各个级别的官员请愿的诉讼状和书信,本文把它们统称为请愿书,因为根本无法区分哪些是书信,哪些是诉讼状,它们的行文结构几无二致。本文节选其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请愿书作一分析。
首先,诉讼者可以向国王提起诉讼,因为国王本身就是最大的法官。(58)例如,公元前145年或公元前116年,大总督等地方官员旅行到菲拉时,从伊西斯神庙祭司那里索取财物,引起了祭司们的不满。因而,祭司们向托勒密八世请愿,请求国王不要让这些官员继续为非作歹,以便他们可以有足够的资源代替国王及其孩子们“向最伟大的诸神提供牺牲和祭品”。(59)即使在村庄里,社会最底层的人们在受到伤害或不公正待遇时,也可以向国王请愿,请求其公正审理案件。例如,公元前220年,一个村民的女孩在洗澡时,受到一位混进女澡堂的男子的袭击。那个男子把一大罐滚烫的热水倾洒在女孩身上,烫伤了女孩的“胸部和左腿直到膝盖的部分”,“生命危在旦夕”。因此,女孩向国王请愿,请求国王命令总督和警察(60)处理此事。(61)这份请愿书的主人公希望国王以最高法官的身份命令地方官员(具有司法审判的职权)公正地审理案件。
尽管司法事务原则上由地方权威人物代替国王处理,但很多请愿还是由国王亲自审理。例如,公元前158年,一位修士托勒缪斯代替弟弟向国王请愿,希望国王可以使一个已故雇佣兵(请愿者的父亲)的后代获得公正对待,使修士及其弟弟获得体面的生活条件。(62)这份请愿书比较特殊,涉及的不是普通人之间的法律诉讼案件,而是个人与国家或者说与国王之间的利益冲突,针对的是国王对待军人及其后代的政策问题。托勒密埃及老兵及其后代的待遇问题是国王们非常关注的。显然,这样的请愿要由国王亲自做出裁定。国王也确实亲自处理某些重大司法事件。例如,下面的一段纸草文献是国王托勒密二世下达的制裁辩护者的敕令。一些辩护者引起了财政问题,给国家收入造成了损失,所以国王“命令:那些辩护者应向王室支付两倍的税务,即多加收十分之一,他们不允许再次在任何事件中作为辩护者出现。而如果这些已危害了财政收入的人中的任何一位被发现在某个案件中从事辩护活动,那么就把他放到我们的监视之下(即打入监牢),并将其财产收归王室”。(63)
在托勒密埃及人的观念中,国王不仅仅是处理财政事务的君主,还是人格神化的最高统治者,是整个埃及的主人。所有埃及人都无条件地臣服于国王,才可以得到正义和公正,才能够得到生存的条件。所以,社会最底层普通农民的案件也希望得到国王的公正审理。下面一篇请愿书是由一位年迈而又受着疾病折磨的老父亲提交的,意在状告自己的女儿,请求国王做出公正的裁决,使他获得应有的赡养:“我正受到狄奥尼苏斯和我的女儿奈克的不公正对待。因为,尽管我已经养育了她——我的亲生女儿,教育她并把她养大成人,但当我被疾病侵蚀和视力衰弱时,她不愿为我提供生活必需品。当我有幸在亚历山大城获得审判时……她在国王作证的情况下向我立下文字誓约:她将通过自己的体力劳动每日付给我20德拉克马……然而,现在,那个犯下鸡奸罪行的狄奥尼苏斯导致其堕落,她不再履行自己的任何诺言,轻视我年老体弱。”(64)虽然在通常情况下,这样的请愿书可能到达不了国王那里,只是在下层官吏那里处理,但这份请愿书一定到达了国王那里。因为我们从请愿书中发现了这样一句话:“当我有幸在亚历山大城获得审判时……她在国王作证的情况下……”,这句话清楚地表明老人曾向国王提起诉讼,而且诉讼得到了国王的受理,国王为他伸张了正义。
其次,更多的情况是诉讼当事人向地方官员提交请愿书。因为在托勒密埃及,某些地方官员也行使法官的职责。(65)比如,一封请愿书是一位运动员向警察或总督提起的诉讼。这位运动员在这里叙述的情况是典型的邻里矛盾。他说:“昨天晚上,厨师阿哥苏斯·戴蒙的妻子戴狄米路过我家,发现我与家人待在一起,便用一种似言非语的腔调傲慢地对待我们——她是一位极度无耻和傲慢无礼的人。就在我阻止她并劝她离开我们时,她变得几近疯狂,借着模糊的夜光,突然跳到我跟前,我没有料到她会有这样的举动。她甚至伸出手来打我,并疯狂地责骂被我喊来做证的外孙们,不仅对他们如此,对当时在场的一位官员也是这样。已经遭受了这样的痛苦,作为这次人身攻击的受害者,我向你投递这封请愿书,请你下达命令把她带到你的面前,以便我能够感受到你对所有人的仁慈。”(66)当时,总督和代总督都具有维护社会治安的职责,同时还可担任法官。(67)这样的请愿书也许送给总督或代总督,或送给警察,或者同时送给他们每一个人。请愿者希望官员伸张正义,主持公道。类似的例子很多。比如,公元前254或前253年,地方财政官和书吏向一位雇佣兵的父亲征收税务时,标准不符合实际情况,比实际的标准高出了很多,引起了雇佣兵与官员的矛盾,雇佣兵代替父亲向中央财政大臣的辅臣递交了请愿书,希望后者主持公道,命令地方财政官和书吏按正确的标准向他父亲征税。(68)公元前114年,一位承包商向村书吏请愿,他怀疑村民西索伊斯家中藏有油料,在中央财政大臣的代理人的陪同下搜查其房屋时,承包商受到了西索伊斯及其妻子的殴打;接下来,当承包商与警察们在神庙外面试图逮捕西索伊斯时,却受到了西索伊斯及其朋友们的围攻。所以承包商希望村书吏能够去收取罚金。(69)
托勒密埃及的请愿书很多,这里仅仅列出了几个最具代表性的案例。请愿书所涉及的案件范围非常广泛,几乎包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诉讼人包括村民、商人、雇佣兵、祭司、王田农夫等。请愿书结构非常一致:开始部分交代请愿者的身份、名字和住址以及请愿的对象;接下来说明事由;最后是希望请愿的对象做出什么样的裁决。请愿所涉及的内容如此之丰富、诉讼人的范围如此之广泛、请愿书的格式如此之固定,都说明请愿是托勒密埃及的主要诉讼方式。
这种诉讼形式使诉讼者具有很大的自由空间,他们可以选择自己所要请愿的法官,可以依据法律选择诉讼机构,更可以选择自己的案件所适宜的法律。请愿与“法官”的受理之间较为直接、简便,不需要很多的中间程序,显得较为和谐。同时,所有的请愿都是为了从国王和官员那里获得正义,希望弱者得到保护,作恶者得到惩治,使混乱的状态归于和平与宁静。无论是国王和官员,还是诉讼者,都希望实现社会和谐。这样的诉讼形式和内容也是法律所赋予的。但同时,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这种诉讼形式。虽然人们可以自由地向自己信任的法官、官僚甚至国王递交请愿书,案件的审理也较为简便和直接,但这也容易造成官员滥用权力和腐败,(70)恰恰暴露了这种诉讼制度的不健全。
五、托勒密埃及的司法审判
从流传下来的纸草文献中,我们可以窥见托勒密埃及一般的司法审判程序。一般来说,托勒密埃及发生争端的双方中的一方向法庭、国王或官员提出诉讼(以请愿的方式,或以请愿书的形式)。接下来,法庭进行处理,送传票给另一方。然后,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庭审。庭审是最关键的一步。在庭审过程中,诉讼双方在法庭上提出各自的证据,为自己辩护,法官们根据辩护和法律做出裁决。最后,法庭的判决得到执行。
下面是法庭在接到请愿书以后对另一方下发的传票。公元前270年之前(具体时间不详)的一张传票,以原告陈述诉讼事由的形式发出,即“尽管我(原告)经常向你(被告)索要这笔钱,但你却不还给我,并拒绝向审计官承认此债务,因此我对你采取司法程序,为了本金和利润共计1050德拉克马,因为损失的估价是1050德拉克马。传票。见证人……。……年,……月14日。案件将在你所在的赫拉克利奥坡里斯的法庭用文书向你提起诉讼”。(71)这份传票确实由法官发出,只是形式有些怪异而已。
接下来是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庭审。从下面一则司法审判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司法审判程序的蛛丝马迹。公元前172年6月11日,在孟菲斯25名祭司组成了一个法庭,对某一案件进行审判:“普塔神庙里面负责记录的祭司中的长者们,与PN在一起,坐在前院(也许是普塔神庙),主持会议。PN是国王的代理人,神庙的监督者(也许是王室的代总督)。普塔的书吏宣读了文件。他们匆忙地把文件送到亚历山大城,决定这些事件习惯上适用于哪项法律……他们把阿庇斯神的仆人们和鹰神的仆人们都带到前院。他们审判了6位有罪的人……他们把罪犯投进了监狱……他们把检察员从阿庇斯神和荷鲁斯神的其他房屋内公开地带到祭司们面前……”(72)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些线索。首先,这25名祭司组成的法律审判会议,受到托勒密国王任命的代理人PN或代总督的监督,后两者都是希腊人。其次,也许像孟菲斯这样特别重要的埃及城市设有法庭,但更可能是为了处理特殊的案件而临时组成的法庭。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法庭的法官“仅仅在某些神庙或城镇中举行他们的审判会议”。(73)再者,司法审判程序很繁琐,至少要先立案,再开庭审理。在庭审过程中,书吏要“宣读文件”(案件内容),然后到亚历山大城获得批复,以决定此案件适用于哪项法律。这项程序可能是形式上的,实际上法官很清楚他们面对的案件适用于哪项法律。然后再进行审判,最后获得审判结果。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只是一般的程序,其具体过程必定很复杂。我们还可以看一个更为详细的庭审案例。大约在公元前226年,托勒密十人法庭(或混合法庭)进行了一次庭审,这次审判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首先在接到请愿书之后,根据审判需要,即“赫拉克雷亚(被告)在请愿书中请求国王组建一个全体法官的法庭……除了每一方根据法律反对的法官以外”,设立了由“狄奥米德斯、伯利克里斯、阿德伦、提奥法尼斯、迈德里乌斯、索尼乌斯和狄奥特里夫斯等人”组成的法庭。接下来,十人法庭根据诉讼状发出了传票,传票交代了诉讼的原因,即原告受到了被告的辱骂和殴打,原告因此损失了200德拉克马,传票还交代了证人和诉讼法庭的地址。然后,“鉴于原告狄奥多图斯既未亲自出现,也未进行文字陈述,也未打算为他的案子辩护;鉴于赫拉克雷亚与她的护卫阿里斯提得斯一起出现,提供了陈述和辩护文案,也打算为自己的案子辩护;鉴于赫拉克雷亚在辩护文案中提交的法律条文,引导我们以一种……方式……进行审判”。最终根据法律规定,即“当两方都被传唤到法庭面前时,如果他们中的一方不愿提供文字陈述或为自己的案子辩护或承认失败……那么这一方将被判处侵犯他人权利罪”,从而“我们已经结案”。(74)也就是说,由于庭审时原告没有出现,而被告则主动积极地进行辩护,从而法庭判决原告败诉。
在庭审中,辩护双方会被要求提供证人和证词。例如,公元前245年,一个证人提供了这样的证词:
阿莫尼安德莫的阿波罗尼德斯的儿子尤弗鲁纽斯,为安特雷特作证人,35岁,高个,粗壮,卷发,白色皮肤,圆肩,右眉间有一痣(?)。在菲拉戴尔夫斯时,我住在阿尔茜诺诺姆。在第2年的帕内姆斯月,当我和尼克恩以及其他一些人正在尤多修斯的理发店时,安提帕特尔和西农(我就是为他们作证)进到那家店铺里,并要求尼克恩交出他们的儿子提奥多修斯,而正在被安提帕特尔起诉的这个尼克恩,否认他已经从他们那里带走了男孩或正以任何条件供养他,(签字)尤弗鲁纽斯(的证词)。(被告)第2年,乔皮提乌斯月26日。为在反对尼克恩(Nicon)案件的安提帕特尔作证。(75)
证词是很正规的,首先交代证人的体貌特征、名字、住址、身份、年龄,接下来说明作证的时间、为谁作证、自己所见的事件经过和结果,最后签字,并强调自己是在为谁作证。这种证词对于案件审理过程是至关重要的,有了证人和证词,法官便可以根据法律和事实作出判决。
宣判之后,审判结果被执行。公元前136年(或许是公元前83年),一份执行审判的命令首先说明了原告和被告的身份、诉讼的事由,然后还交代了审判的依据,最后命令“外国债务的收集者”负责执行法庭的判决:“我们已经判决:请愿者的要求得到承认,而且一个命令应该被写给下面提到的收集者,去为他收取……款项和附加项目。”(76)
托勒密埃及的司法审判程序是较为完善的,一环扣一环,紧凑而又合乎逻辑。尤其在庭审结束以后,还要依靠强制手段确保庭审结果的遵守,确保了正义的伸张,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和受害者或弱势方的利益。整个诉讼过程都是以法律为基础的,体现了法律及司法实践的和谐性,这一点不容置疑。虽然这种和谐是潜在而被动体现出来的,“和谐”并非托勒密国王所能提出的理念,更非其制定和实践法律时有意达到的一种目标,但托勒密埃及的法律毕竟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弱者的利益,惩治了作恶者,从而使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归于安宁与平静。
六、结论
从整体上看,托勒密埃及的法律是很特殊的,其形成基础、内容及司法实践都是由两种不同的因素构成的,这两种因素并行发展,但在国王和官僚介入的情况下,法律及司法实践基本能够达成和谐。托勒密埃及为什么能够保持法律及司法实践的“二元性”和“和谐性”呢?从历史学的角度看,这具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根源。
首先,托勒密家族以及跟随而至的马其顿人、希腊移民是统治阶级,但他们毕竟是外来族群,埃及本来的主人是本土埃及人,更何况在亚历山大离开埃及之后和托勒密一世接手埃及之前,实际统治埃及的是克里奥美尼斯,后者在埃及推行的政策是反人民的,引起了埃及人的强烈不满。(77)故而,如何使土著埃及人接受马其顿人和希腊移民的统治,如何调节马其顿人、希腊移民与本土埃及人的关系等,便是摆在托勒密埃及统治者面前的重大问题,这是内政问题,也涉及族群问题,解决的好坏直接关系托勒密王朝的存亡。在这种情况下,从法制上保持“旧制”,尊重各个族群的法律传统,允许两种法律并存,而不强行统一法律,便是解决族群矛盾的切实可行方式之一。
其次,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是掠夺性的,使埃及遭受了沉重损失。(78)如前所述,亚历山大任命的克里奥美尼斯的统治也是不得人心的,使埃及的经济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可以说,托勒密王朝接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百业待兴的埃及。如何促进经济的发展,也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经济的发展必然需要法制的规范。托勒密埃及不同族群的人们在经济活动中需要签订各种契约。他们在签订契约时仍然习惯于运用自己的母语和自己熟知的法律。因此,保持两种法律和司法实践的并行发展,并在国王的参与下使两种法律达成和谐,便可以很好地满足这种经济活动的需求。
再次,在托勒密埃及,统治阶级是希腊、马其顿移民,他们也是社会的第一等级,享有各种特权;被统治阶级是埃及当地人和其他外来移民,他们属于第二
等级。在第二等级中,还有一个埃及当地祭司和地方贵族阶层,他们充当了统治埃及的工具,当然也享有一定的权力,其社会地位相较于普通土著埃及人要高一些,他们是第二等级中的上层。第二等级的下层,即社会的最底层,是普通埃及当地人和其他外来移民。“整体上,埃及人已从领主降为低级劳动者,降到了社会第二等级,在它之上是一个希腊人阶层。”(79)一部分埃及当地人可以借助财富和知识进入一个较高的社会等级,但他们必须接受教育,深谙希腊文化。比如马涅托,他显然既懂希腊文又懂埃及文,而且对两种语言都很精通,才获得重用。而埃及人中能够接受教育的人并不多,只有那些社会上层人士和富有者才有这样的机会。因而广大的下层农民仍然生活在他们的传统世界里,保持他们古老的传统和生活模式,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制定契约。(80)这种等级和阶级关系也使托勒密埃及不能建立统一的法律和司法制度。
最后,在托勒密埃及,两种文化背景的人们生活在一起,希腊城邦移民和马其顿人具有民主制背景,西亚移民和埃及本土人受君主制影响较大。希腊城邦移民和马其顿人必然不习惯埃及本土法律,而埃及本土人必然对希腊法律感到陌生。因而,托勒密埃及很难实施一套适用于两种文化背景的统一法律及司法制度。保持两套法律并行发展,使其在发展过程中自然地相互影响和相互融合,可能更适合托勒密埃及的社会现实。事实也证明托勒密国王所采取的法律和法制政策是正确的。
然而,我们也不能过高评价这种法律的和谐性。事实上,这种法律完全是出于统治的需要。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托勒密埃及的法律实际上是国王为了更好地进行统治而建立起来的,始终受到国王的控制。法律的条款没有通过任何集体的讨论,而完全是国王个人意志的体现。无论是原有的法律,还是国王颁发的敕令和赦令,其实施的前提条件都是法律必须符合国王的意愿。法律诉讼和审判都要维护国王的利益,国王、王室和统治阶级的利益不容侵犯。可以说,托勒密埃及的法律是为专制王权服务的,法律及其实践是托勒密国王对埃及实行专制统治的需要,也是托勒密埃及专制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81)
注释:
①学界一般把公元前323年之前的埃及称为“法老埃及”。
②尽管托勒密埃及是古埃及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阶段,但学者们习惯称这一时期的统治者为“国王”而非“法老”,这主要是为了从统治者的称谓上把较少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法老埃及与受希腊文化影响较深的托勒密埃及区分开来。实际上,托勒密埃及国王的权威不仅不比法老埃及时期的法老弱小,反而更强大。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郭子林:《论托勒密埃及的专制主义》,《世界历史》2008年第3期;《论古埃及托勒密王朝王权与神权的关系》,《古代文明》2008年第4期。
③R. Taubenschlag, The Law of Greco-Roman Egypt in the Light of the Papyri, 332 B.C. -640 A. D., New York: Herald Square Press, 1955, pp.21-27.虽然作者在罗马法研究领域造诣精深,但对托勒密埃及的法律状况了解不够。当然,这也与当时托勒密埃及史的研究水平有限不无关系。
④这里的“希腊城邦移民”采取广义概念,不仅包括希腊大陆和爱琴海诸岛屿城邦的移民,还包括环地中海地区希腊殖民者建立的殖民城市国家的移民,例如小亚细亚一些希腊城邦的移民。当然,本文为了突出马其顿人的统治阶级身份而单独叙述之,并非暗示马其顿人与希腊城邦移民的族群(ethnic)差异。事实上,从语言、宗教、名字、习俗等方面来看,希腊城邦移民与马其顿人属于同一个族群(W. Clarysse, "Ethnic Identity in Graeco-Roman Egypt," ~tebtunis/lecture/wclarysse_exhibit.html)。另外,本文在谈及不同的人群时,一般采用“族群”二字,而不使用“民族”(nation)一词,也不使用“种族”(race)这样的称呼,因为古代世界没有严格意义的民族;种族概念似含贬义,甚至已被最近30年考古学、人类学、比较语言学等学科的学术研究所证伪;而唯独“族群”最能恰如其分地表达古代世界不同人群的划分。
⑤古代西亚移民主要是波斯入侵埃及时(前525—前404年和前343—前332年)随之而来的移民,托勒密埃及的文献一般把这些移民称为波斯人(W. Clarysse, "Three Soldiers' Wills in the Petrie Collection: A Reedition," Ancient Society, vol. 2 (1979), pp.12-13)。也有学者把这些移民称为叙利亚人(S. M. Burstein, The Reign of Cleopatra, London: Greenwood Press, 2004, p.44)。
⑥S. M. Burstein, The Reign of Cleopatra, p.44; M. M. Austine, The Hellenistic World from Alexander to the Roman Conque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981, pp.453-454.
⑦R. Chadwick, First Civilizations: Ancient Mesopotamia and Ancient Egypt, London: Equinox, 2005, pp.55-56,64;刘家和、廖学盛主编:《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6-93页。
⑧约翰·H.威格摩尔:《世界法系概览》(上),何勤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2页。
⑨D. M. MacDowell, The Law in Classical Athen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Ltd., 1978, pp.41-52.
⑩约翰·H.威格摩尔:《世界法系概览》(上),第224-296页。
(11)M. J. Cary and T. J. Haarhoff, Life and Thought in the Greek and Roman World,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40, p.23.
(12)提奥多里泰斯就曾指出:“一个敢于谈及古代埃及法律的人,必然会使自己遭受许多批评”,很多埃及学权威人士认为埃及法律“缺乏文献上的证据”。A. Théodoridès, "The Concept of Law in Ancient Egypt," in J. R. Harris, ed., The Legacy of Egyp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243.
(13)J. H. Breasted, A History of Egypt, New York: Scribners, 1905, p.242.
(14)R. VerSteeg, Law in Ancient Egypt, Durham: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2002, pp.3-7.
(15)C. F. Nims, "The Term Hp, 'Law, Right', in Demotic,"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7 (1948), p.243.
(16)C. F. Nims, "The Term Hp, 'Law, Right', in Demotic," p.243; D. B. Redford, ed.,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Ancient Egypt, vol.Ⅱ,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279.
(17)Herodotus, The Persian Wars,Ⅱ, 113, trans. A. D. Godle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2.
(18)Diodorus Siculus, Library of History, I, 77-8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19)W. F. Edgerto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Governed in the Egyptian Empire,"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 6(1947), p.154.
(20)R. VerSteeg, Law in Ancient Egypt, pp.3-14.
(21)C. F. Nims, "The Term Hp, 'Law, Right', in Demotic," p.245.
(22)R. VerSteeg, Law in Ancient Egypt, p.21.
(23)S. Allam, "Law," in Toby Wilkinson, ed., The Egyptian Worl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p.264-267.
(24)R. VerSteeg, Law in Ancient Egypt, pp.99-216.
(25)Diodorus Siculus, Library of History, I, 94:1-4.
(26)刘文鹏:《古代埃及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96页。
(27)Herodotus, The Persian Wars, II, 136.
(28)刘文鹏:《古代埃及史》,第204页。
(29)维西尔(Vizier)是法老埃及的最高官职。
(30)M. J. Geller, et al., eds., Legal Documents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 London: The Warburg Institute in University of London, 1995, p.2.
(31)Diodorus Siculus, Library of History, I, 75.
(32)M. J. Geller, et al., eds., Legal Documents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 p.2.
(33)B. G. Trigger, et al., Ancient Egypt: A Social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84.
(34)J. R. Harris, The Legacy of Egypt, p.268.
(35)Diodorus Siculus, Library of History, I, 94-95.
(36)Diodorus Siculus, Library of History, I, 95.
(37)M. J. Geller, et al., eds., Legal Documents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 p.3.
(38)S. Allam, "Law," in Toby Wilkinson, ed., The Egyptian World, pp.268-270.
(39)M. J. Geller, et al., eds., Legal Documents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 p.5.
(40)M. J. Geller, et al., eds., Legal Documents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 pp.7, 10.
(41)M. J. Geller, et al., eds., Legal Documents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 p.11.
(42)M. J. Geller, et al., eds., Legal Documents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 p.10.
(43)R. Taubenschlag, The Law of Greco-Roman Egypt in the Light of the Papyri, 332 B.C. -640 A. D., chapters 2-5.作者列举了许多纸草文献,间接体现了希腊罗马统治时期埃及的法律形式。
(44)转引自约翰·H.威格摩尔:《世界法系概览》(上),第15-17页。
(45)道本施莱格在其著作中列举了大量希腊文和世俗语的法律文献,并分别叙述了希腊罗马统治时期埃及的私法、刑法、司法程序以及执行,其中有些内容体现了托勒密埃及的法律内容。参见R. Taubenschlag, The Law of Greco-Roman Egypt in the Light of the Papyri, 332 B.C.-640 A. D., chapters 2-5.
(46)G. P. Goold, ed., Select Papyri, vol.II, trans. A.S. Hunt and C. G. Edga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pp.7-9.
(47)G. P. Goold, ed., Select Papyri, vol.II, pp.11-39.
(48)M. M. Austine, The Hellenistic World from Alexander to the Roman Conquest, pp.382-387.
(49)R. S. Bagnall,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apyr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544.
(50)R. S. Bagnall,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apyrology, p.556.
(51)H. I. Bell, Egypt from Alexander the Great to the Arab Conque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p.34; J. G. Manning, Land and Power in Ptolemaic Egyp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53.
(52)M. J. Geller, et al., eds., Legal Documents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 p.7.
(53)M. M. Austine, The Hellenistic World from Alexander to the Roman Conquest, p.386.
(54)P. Jouguet, Macedonian Imperialism and the Hellenization of the Eas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313.
(55)P. Jouguet, Macedonian Imperialism and the Hellenization of the East, p.315.
(56)F. W. Walbank, et al.,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V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8, p.120.
(57)请愿是法老埃及司法诉讼的传统方式之一。例如在《能言善辩的农夫》这篇文献里,主人公库纳努朴(Khunanup)因为不满大总督的判决而直接向法老申诉,最终获得胜利(I. E. S. Edwards, et al.,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465)。
(58)F. W. Walbank, et al.,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VII, pp.119-120.
(59)S. M. Burstein, ed. and trans., The Hellenistic Age from the Battle of Ipsos to the Death of Kleopatra V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42.
(60)大约最早在法老埃及第十二王朝时期,努比亚人的一部分麦德查人便充当沙漠警察;到第十八王朝时期,麦德查人成为名副其实的警察,在总督的领导下巡逻沙漠、警戒墓地。新王国时期,埃及的每个诺姆都配备着警察(I. E. S. Edwards, et al.,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370)。古代希腊城邦也已经出现了警察,一般由奴隶充任,独立于军队系统之外(M. J. Cary and T. J. Haarhoff, Life and Thought in the Greek and Roman World, p.130)。托勒密埃及的警察由希腊移民或希腊化的埃及本地人充任,直属诺姆的总督或代总督管理,独立于其他官员和军队之外。当然,古代世界的警察与19世纪之后的现代警察在制度和职务上都存在差别。
(61)G. P. Goold, ed., Select Papyri, vol. II, pp.235-237.
(62)G. P. Goold, ed., Select Papyri, vol. II, pp.243-245.
(63)S. M. Burstein, The Hellenistic Age from the Battle of Ipsos to the Death of Kteopatra VII, pp.121-122.
(64)M. Chauveau, Egypt in the Age of Cleopatra, trans. David Lorton,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p.58.
(65)F. W. Walbank, et al.,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VII, p.120.
(66)S. Eitrem and L. Amundsen, "Complaint of an Assault, with Petition to the Polic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vol.40 (1954), p.31.
(67)F. W. Walbank, et al.,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VII, p.120.有关托勒密埃及官僚体系的构成和官僚的职责,参见郭子林、李岩:《托勒密埃及官僚制度探微》,《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68)G. P. Goold, ed., Select Papyri, vol. II, pp.227-229.
(69)G. P. Goold, ed., Select Papyri, vol. II, pp.253-255.
(70)托勒密埃及确有官员滥用权力和腐败的案例。例如,一篇文献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要特别注意,不要有任何舞弊行为。”(M. M. Austine, The Hellenistic World from Alexander to the Roman Conquest, p.432)另外一篇文献记载了明目张胆的贿赂行为:“根据你的指示,我们已经为克里斯普斯(国王的护卫长)和首席财政大臣的来访准备了10只白头鸟和5只家鹅;(我们有)50只野鹅,200只野鸡,100只野鸽子;我们还借了5头用于骑行的驴……而且,我们也准备了40头用于驮运物品的驴;我们正准备去接他们。”(M. M. Austine, The Hellenistic World from Alexander to the Roman Conquest, p.428)在古代埃及当时的生活条件下,地方官员为中央官僚提供如此多的物品,除了行贿受贿行为,恐怕没有其他更好的解释了。这种官员受贿的行为与法律诉讼形式的不健全有很大关系。
(71)G. P. Goold, ed., Select Papyri, vol. II, p.173.
(72)S. Allam, "Egyptian Law Courts in Pharaonie and Hellenistic Times,"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vol. 77(1991), p.120.
(73)S. Allam, "Egyptian Law Courts in Pharaonic and Hellenistic Times," p.119.
(74)G. P. Goold, ed., Select Papyri, vol. II, pp.191-195.
(75)G. P. Goold, ed., Select Papyri, vol. II, pp.185-187.
(76)G. P. Goold, ed., Select Papyri, vol. II, pp.221-225.
(77)亚历山大离开埃及之前设立了两个总督,以期互相牵制(Arrian, Anabasis of Alexander, III, 5:7, trans. P. A. Bru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其中一个是埃及本土人,另一个是希腊人克里奥美尼斯。后者最初只是掌握全国的财政大权,后来把包括沙漠地区在内的整个埃及财政都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实际上控制了整个埃及(W. M. Ellis, Ptolemy of Egyp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8)。他在埃及期间实施了一系列不得民心的政策,例如克扣雇佣兵的军饷,从埃及祭司手中榨取“保护费”,甚至对运往希腊应急的粮食征收关税,这些税收和贡赋都成了他自己的财产(W. M. Ellis, Ptolemy of Egypt, p.30)。
(78)R. Chadwick, First Civilizations: Ancient Mesopotamia and Ancient Egypt, pp.224-225.
(79)L. Casson, Everyday Life in Ancient Egypt,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37.
(90)H. I. Bell, Egypt from Alexander the Great to the Arab Conquest, pp.42-43.
(81)关于托勒密埃及专制主义的特点,可参见郭子林:《论托勒密埃及的专制主义》,《世界历史》2008年第3期。
转自《历史研究》(京)2010年4期第4~18页
责任编辑:刘悦
分享到: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
上一篇:古代世界的共和主义
下一篇:中世纪英国宪政制度新解
最新更新
猜你喜欢
关注我们


 当代时讯
当代时讯  中国历史
中国历史  世界历史
世界历史 历史典故
历史典故  历史百科
历史百科  野史秘闻
野史秘闻  民间故事
民间故事  神话传说
神话传说  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  网站首页
网站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