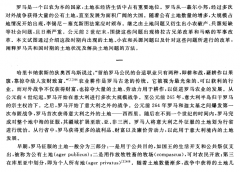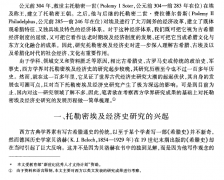中世纪英国宪政制度新解
作者简介:
文学与历史:质疑中世纪英国宪政制度
理查德·卡尤珀
【英文标题】A New Interpretation of Constitutionalism in Britain in the Middle Ages
【作者简介】理查德·卡尤珀,罗彻斯特大学中世纪史资深教授,卡尤珀教授的著述甚丰,专著主要有:《借贷给王权的银行家:卢卡的雷克卡迪和爱德华一世》(Bankers to the Crown: The Riccardi of Lucca and Edward Ⅰ,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3)、《战争、正义与公共秩序:中世纪晚期的英国与法国》(War, Justice and Public Order: England and France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中世纪欧洲的骑士与暴力》(Chivalry and Violence in Medieval Euro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神圣的武士:骑士阶层与宗教》(The Holy Warrior: Knighthood and Religio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9)。——译者注
半个世纪以前,威廉·卡罗尔·巴克(William Caroll Bark)曾声称:“在众多的历史学家中,皮朗(Pirenne)因他提出的问题而成为最受尊敬的历史学家之一。”尽管我没有皮朗的成就,事实上也不能与其学术成就相媲美,然而我还是要围绕我们的议题提出一系列问题。当然,与我所提的问题相比,所有感兴趣的学者都会提出更为基本的问题:他们经常争论中世纪英格兰民众实际上是如何被统治的,法律是如何制定和执行的,在特定历史时期各个社会阶层有何普遍反应。
在阐明我的看法之前,我首先需要声明一点:我们没有必要因为自己另类的学术观点而深表歉意。对统治、法律、正义与宪政主义的深入研究似乎已经过时,所有研究不都在斯塔布斯“主教”及其追随者那里完成了吗?在此,我想表达(我认为是)我们唯一的共同信念:我们所探讨的是学术研究中最重要、也是最持久的问题。我想强调,长期的乃至一生的学术经历,甚至近些年的研究,都已清晰地表明这些探索是多么重要。在我们的学术传统中,研究先辈文明的最初形态以及他们暴风骤雨般的生活,是一项具有重大价值的学术努力。可以这样说,这项探索要求很高,需要掌握一整套技巧去解读普通法以及建构英国统治秩序的复杂机制。同样,它还要求研究者掌握一系列卷帙浩繁的证据,而对这些证据的解读却是众说纷纭。这些证据已经对数十年来轻易得出的学术结论提出了挑战。尽管这类证据看起来似乎篇幅浩大,但实际上却是不充足和不确定的。因此,当其中充满复杂性时,学者们的观点很容易发生分歧。
事实上,到现在为止,我提出的最关键问题是证据的选择和运用。历史学家可能更容易与那些受人尊敬的文学同事为伍,现在所谓“文学转向”的最激进阶段已演变为一个日益成熟的转型阶段。所有人文科学领域中那些重燃激情的学者都在激烈地争论着我们的文本(不论是诗歌、编年史、令状、法庭卷档和记录)中那些让人难以把握的思想,因此,跨学科的讨论不太可能关注后现代理论,而是更多地关注两个令人棘手但又交叉的原始证据问题。任何学者在这些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如何研究我将要提出的所有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令人信服地辨别典型的证据?答案绝非不言自明。究竟需要多少文献才能构建出一种模式或趋势,以证明社会、文化的停滞与变迁?在我们早期的调查研究中,这个问题相当麻烦,因为很多证据早已丢失。甚至到了14世纪或15世纪,就有关于法律实施、乡村(和城市)暴力与失序的生动而又零散的证据,推测这些证据的真实性与权威性很成问题。25年前,对犯罪指控和定罪率的严格量化似乎是一个颇有希望的解决办法,但事实却证明这是非常令人失望的。把编号为Off8ce的文献(现存于克尤的国家档案馆)上的信息输入计算机,无论这是多么有魄力甚至英雄般的尝试,它也没有使学者达成广泛共识。虽然现存的证据零散,却依然很重要。如果我们有这些证据,无论其是否完整,也可能很好地记述了有关政治和财政目标的诉讼模式。在我们这个更为数字化的时代,获取得到更好保存的犯罪统计资料同样也是真实的,至少在粉碎机发明之前是这样。再者,我们有时也会怀疑,失序是否与犯罪联系在一起?难道我们不应该考虑到社会精英阶层的暴力行径吗?与无特权的邪恶之徒的普通罪行相比,社会精英阶层因暴力行径而受到的指控要轻得多,而且对社会精英的指控也不严格遵照既定的规矩。尽管记录前者人身攻击、偷盗等行为的档案装满了羊皮口袋,可这并不意味着精英阶层当时正在举行祈祷会或者在品茶。
从何处寻找证据?这可能取决于我们如何认识法律的制定。我们会以为法律在某种意义上是自我产生和演化的吗?也就是说,我们能将法律视为由自身内在理路以及固有原理的拓展所推动的知识体系吗?抑或我们宁肯如同对待真理一样,认为法律是时间的婢女,是每一时代客观历史力量作用的产物,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明显是为了那个时代特定阶层的利益而刻意设计的吗?不同诠释立场之间的鸿沟因此而扩大了。它是确凿证据使然吗?抑或,是某种知识、社会、甚至道德的倾向决定了辩论各方必然坚持非此即彼的坚定立场吗?当研究形成中的国家机器及其与各种正义观念和理想之间的关系时,我们阅读过历时数世纪之久的客观证据吗?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国家效能和国家适当作用的任何现代认识,不都是戴着有色眼镜而得出来的吗?此种担忧从历史学家一开始进行探索时就已经困扰他们了。当然,最近对此最为忧虑的要数我们的文学同仁了。
当论及第一个问题的另一面时,同样存在学术分歧。我们在研究中能够(事实上我们必须)利用当时(即中世纪)的文学作品吗?或者,即便那些极不情愿的历史学家认为我们应该利用文学作品,那么我们在研究社会、政治和法律时又该如何评估和使用文学证据呢?既然形形色色的文化研究似乎已经剔除了可能导致一系列对立的理论倾向的因素,那么,历史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各自路径就可以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吗?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能够找到一种共同语言来实现共同目标,以此丰富这两个学科吗?诚然,几个世纪以来,富有想象力的文学作品不断堆积成为一座熠熠闪光的证据宝藏。在我的印象中,研究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学者就已经在开采这座宝藏,而研究盎格鲁诺曼时期的学者在这方面做得相对不够充分。随着研究英国中世纪晚期文化的学者开始探讨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文本(这些文本建构了那个时代的特征),讨论变得更加复杂了。难道我们不是正在目睹实际的社会趋势或不断增多的残存证据吗?中世纪晚期文学作品得到广泛传播是毫无疑问的:我们拥有许多反映社会各阶层生活的文学作品,从乔叟、高尔、郎兰、英伦半岛式的浪漫生活、罗宾汉的故事,一直到粗俗冗长的文学作品(奥斯特准确地称之为讽刺文学和控诉文学)。由于这些文学作品都是虚构的,历史学家在使用它们理解法律和统治的运行时就遇到了相当大的麻烦。因此,学者又转而讨论证据是否是可接受的、真实的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尤其是控诉文学,它可能被解读为心怀不满和失落的个人所发出的声音,而不是表达整个社会的呐喊,因而其史料价值大打折扣。然而,我们也可以把它们解读为是对社会普遍不满的一种反映,这些作品最终帮助我们冲破了那堵妨碍我们理解久远历史的无声之墙。
而且,这种讨论可能深深植根于我们对人性和人类制度本质的假定。然而,追问这些问题或许是有帮助的,即我们虚构的文学作品是否与其他类型的证据相吻合?特别是这种辅助性的证据是否很少有争议?不同类型证据之间的某些重合可以印证彼此的真实性。例如,我们可以考虑能否用一种视角把控诉文学、罗宾汉的故事和1381年大起义三者联系在一起。我们不能想当然地将大起义仅仅归结到经济史的研究领域。有的学者认为,起义者要求解决的根本问题绝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抱怨。他们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正义观念本身,或者说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了无效的正义和不堪忍受的不公正待遇所导致的威胁。这一观点是基于一系列证据而得出来的:起义者选择的目标;他们提出的要求;动荡后召开的议会上人们所发表的忧虑有加、互相指责的演讲。一些人担心,苛政和不公正普遍存在,并且是引发起义的催化剂。那些在羊皮纸上创作出富有想象力的文学作品的作家们,其所思所想正反映了上述忧虑。我们能用这样一种视角分析这些浪漫主义的文学证据吗?
如果我们在相似的历史案例(它们会涉及一些文学作品以及对法律和统治的普遍反应)中探寻这种视角,我们会获得什么结果呢?我认为,以12世纪《列那狐的故事》为代表的流行动物寓言故事,丰富地展现了人们当时的复杂态度,他们对“准有效统治”在西北欧的盛行表现出了热烈欢迎的态度。《列那狐的故事》表明,君主的积极作用是受到广泛认可的,正如君主的统治让人不寒而栗一样。然而,君主似乎无法有效地确保真正的和平,也无法驯服权势者的激情。通过对骑士文学数十年的广泛研究,我在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以及那些具有很少虚构成分的骑士传记和白话手稿中发现了基本的证据。尽管我们缺少大量回忆录、报纸和私人信函等证据,但是,我建议,我们可以通过小心地利用这些文学作品(它们对当时最重要的事件都有丰富的诠释)来弥补证据的不足。如果这类文学作品不是描述事实而是表达情感,那么它不正是研究人们(这些人的心灵正是我们试图重构的对象)精神状态的最佳证据吗?
试想在一个雨雪敲打窗棂、窗帘被风时时掀起的冬夜,我们到访一个地方乡绅聚会的大厅又当如何?此间,高脚杯斟满了美酒,他们大声诵读文学作品,有关中世纪爱情的争论牢牢地吸引了这些人的注意力,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作品中提出来的重要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如何谈论中世纪英国各个历史时代的公共秩序?这个问题似乎是抽象的、没有定论的,因而自然要激起激烈的争论。然而,我们几乎不能完全回避这个问题。评估相对和平与秩序,或者评估暴力和违法行为的社会、政治甚至文化影响,肯定都是充满争议的。我们迫切需要一个合理的框架来分析这些问题,但我们又很难搭建这样一个框架。
我们可以提出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尽管可能不会赢得普遍赞同。在研究时,我们可能都乐意放弃所有的努力去揭示犯罪的绝对事实,我们甚至不再试图去考察社会精英因长期争斗、剥削、复仇等而引发的暴力。相反,最佳的评判标准是当时人的观点,如果我们能揭示它们的话。因此,这种框架应该分析:当时人们的期望和反应;人们对问题严重性的认识;暴力行为对它们的困扰有多么严重;法律是如何有效应对这些问题的。我们也想知道各个阶层的人士是否认为他们有可能获得公正的待遇,当然,我们也想知道他们眼中的公正意味着什么。显然,随着时空转换和社会地位的变化,当时人的观点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社会对暴力和不公正接受程度的变化而变化。
尽管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但是,回忆数十年前就已指出的证据或许是有趣的,甚至还具有重大的意义:13世纪末或者14纪最初的数年,存在三种不同的声音,它们表达了对国内暴力泛滥现象的担忧。编年史家彼得·兰托夫特(Peter Langtoft)担心:“社会动荡会在王国内引发全面战争。”一位写过一本反映流氓生活诗集的匿名诗人,也做出了同样的预测,他担心这种失序预示着“战争的来临”。当然,他指的是国内战争。如果“持有偏见的编年史家”和“心怀敌意的小册子作者”只是无谓的抱怨,我们可以读一下爱德华一世自己的评论,这些评论记录在他的私人书信(它们被收录在《国库备忘录档案》里)中。爱德华一世责令王室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因为王国中的“无序、骚动以及暴行”可能引发战争和玷污国王的统治权威。这些具有如此不同特征甚至在语言表述上也极其相似的材料,都一致认为问题很严重,那么,我们用这些材料来证明什么呢?这一证据是否更适合解释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一个问题呢?或者难道不是这一很有趣但却间接的证据,揭示了一个在法治和战争上取得巨大成功而又精力充沛的国王在其统治的数年中所面临的困扰吗?
第三个问题是,在普通法实施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到乡绅所发挥的作用。我们能再现他们是如何看待法律、服从法律和利用法律的吗?我们能怀疑他们在中世纪晚期农村地区的法律执行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农村地区的法律和审判又是如何被乡绅掌握的呢?我们随意地给这些问题贴上难以理解和易引起争议的标签,因为回答这些问题,意味着不仅要去理解审理所有案件的古老僵化的巡回法庭消失之后出现的情况,还要去理解治安法官出现之后所发生的事情。
在现代杰出的学术研究中,这些充满活力的乡绅因其忠诚又热心于公益而受到了高度赞誉。而其他一些学术著述却告诫我们:法律作为“矛”的作用丝毫不亚于其作为“盾”或者司法平衡载体的作用,而乡绅们的仇斗是一种一贯的现象。至少我们想知道,侵犯性地私自使用法律权力的现象是否是普遍的。一个崛起的社会集团正在不断累积权势,从而与其在地方上的社会声望相称:在这种法律系统中,这些新获得的能力难道不能被证明是一种用来提升社会影响的无法抗拒的手段吗?
上述讨论自然要过渡到对典型证据问题的探讨,甚至可能最终归根于对人性的一种特定认识。然而,我希望我们能恰当地提出这一问题:通过考察乡绅的社会服务职能以及他们巨大的野心,我们能进入乡绅的精神世界吗?乡绅愿意以法律为工具对抗其对手,或者愿意越过法律直接诉诸暴力,有关这方面的著名例子难道仅仅是一个鲜活的特例吗?比如,猖獗的犯罪团伙中不仅包括约曼农(yeoman),还有乡绅甚至少数的僧侣,我们对此该作何理解呢?我们该把这一事实看成无关紧要的偶发现象吗?著名的《帕斯顿信札》是否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以便了解社会暴力及乡绅阶层对法律程序的态度?抑或人们透过玻璃所见到的只是被扭曲了的流行看法?对于我们来说,再现人的精神世界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就如同我们试图穿越这些争议地区时遇到的荆棘一样。
通过考察中世纪严厉的忏悔制度,我愿意坦诚,我对乡绅、法律、正义三者重要交叉点的印象,始自我对王室特别调查团中法官听审与判决罪犯行为的深入研究。有用的证据不仅存在于法院的记录中,也存在于数以百计的议会请愿书中,这些请愿书现存于国家档案馆中,目录为SC8。尽管我的研究并不关注社会群体,这项研究所收集到的证据涉及1270-1370年间一百年的历史,而且还获得了许多有关乡绅社会地位的证据。有些请愿书不仅揭示出社会精英阶层中存在的严重暴力问题,而且还揭示出:乡绅以及更高社会等级的人都在滥用司法审判权。事实上,许多请愿书不是谋求得到一个调查团的授权,而是要从已经得到授权来伤害他们的敌手那里获得补偿。请愿者以愤怒的语调抱怨说,敌人捏造罪状来指控冒犯他们的人,然后又让他们的亲戚、朋友、附庸及领主当选为法官(这是可以做到的),审判地点选在敌视他们的城堡的城墙下。请愿者甚至害怕出席法庭审判。有些请愿书还生动地写道:张贴出来的告示警告附近的所有人,让他们不要愚蠢地出庭作证以反抗强势的原告,当然了,这些原告也在极力扭曲调查团的意图。
反对的意见又再次出现了。一些学者担心这些请愿书夸大了罪责指控,或仅仅是简单的土地案却被纳入王室司法权的范畴,也就是通过指控敌手“以武力反对国王的和平”,这个案子就归王室法庭管辖了,即使被告仅仅由于“捡起我家果园中的苹果”就可以立案了。那么,解释证据的均衡点在哪里?这些证据的重要性又如何呢?
一种回答可能强调,为了让国王支持或反对法庭而故意夸大或操纵人们的诉求,其结果也会扭曲我们如何理解社会精英人士对法律的认识与利用。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请愿书都应被看成是虚构的,而且,不管请愿书的真实内容是什么,法律程序经常被精英们如短棍般地挥舞利用。他们不仅认为法律对社会秩序与社会和谐负有无比重要的责任,而且他们还将法律视为不断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更坦率地说,这些证据很难让我把乡绅阶层想象成捍卫乡村正义的理想代理人,而他们本应是无私保证乡民普遍满意进而使法律秩序平稳运行的坚强支柱。
当然,既然开启了这一话题的讨论,我就继续袒露我的意见:我对骑士制度的广泛研究(当然是以大量文学作品为基础的)使我将骑士精神归结为是对勇敢和荣誉的崇尚。勇敢意味着高超的武艺,这与优雅与否无关,更不关乎维多利亚精神。我认为在此行为规范下,我们必须认识到,要实施强有力的复仇行动需要投入很多的资源。我认为,如果这种强悍的骑士精神塑造了社会的精英阶层,那么,运用法律还是运用武力去达成他们热切渴望的目标之间难道不存在紧张关系吗?再者,由于这种思想和行为规范可以赋予人们以精英身份,那些渴望乡绅地位甚至更高地位的人难道不会从这种规范中吸取更多的东西吗?
如果对乡绅作用的研究会引起争论,那么对国王作用的研究也是如此,这就引导我提出第四个问题。捍卫正义的核心力量是国王或曰王室管理阶层吗?数个世纪以来,国王在其统治期间介入法律问题的程度改变了乡村的状况吗?与国王置身于法律问题之外相比,当国王干预法律问题时,法律是不是运转得更为有效甚至更为公正?那些给予这个问题以肯定回答的人难道就必须被贴上“国王朋友”的标签吗?
在许多争论中,至少有一种观点是清晰的,尽管其是否有说服力仍然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文学证据。在我们所关注的长达四个世纪左右的历史中,富有想象力的文学作品关注国王为捍卫社会公正而发挥的作用。然而,这些文学作品似乎过分强调了国王的这种作用。如杰弗里(Geoffrey)在其作品《英王史》中滔滔不绝地赞美了那些能够维护和平并制定良法的君主。当然,包括亚瑟王在内的国王们很可能是虚构出来的,但这并不会削弱其中所表征的文化寓意。
我们能够想到自13世纪末期以来涌现出许多用中古英语写成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这些作品表达了人们对强大王权的期盼,希望国王能够严格执行法律、捍卫正义,从而为乡村带来和平。我自己最喜爱的作品是《丹麦人哈弗洛克》(Havelock the Dane)和《加麦林的故事》(Tale of Gamelyn)。前一本书开头的简介部分向我们展示了文学作品在评论王权和法律方面所表现出的风格。在中世纪早期,一个名为奥瑟沃德(Athelwold)的国王制定并且严格遵从良法,他因此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爱戴。这位国王是一位虔诚的教徒,他热爱教会、真理和正义,憎恨一切不法之徒并把他们送上绞刑架,别人的贿赂也丝毫不能阻挠他。正是由于这样,王国内部十分太平,一个人可以携带40英镑之多的货币游走各地,而无需担心被抢劫。诗人欢呼:“在英格兰多惬意!”他们把国王称颂为:“他是英格兰的福祉!”他们还认为国王是不可战胜的:从他的王国到罗马,没有哪个领主胆敢冒犯他的子民,也没有哪个骑士能给国王带来恐惧。任何违法的骑士都会失去马匹和服装,还可能会被迫张开双手谦卑地向国王高声祈求:“君主啊,请宽恕我吧!”可以肯定的是,那个时代许多人的认识只停留在诗歌的表面上,然而,这些诗作对王权与法律之融合的深层强调仍然令人惊奇。
此外,这些富有想象力的文学作品所反映的史实也能在其他类型的证据中得到印证,国王在官方文件中对自己的称颂就是一个例子。王室的宣传(Royal propaganda)经常宣称,国王将会像文学作品所期望的那样进行统治。同时,法令的序言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序言反复强调,国王将把正义与和平铭记于心,并许诺采取大胆的举措来维护王国的和平。
对这些特殊证据的研究还能进一步延伸,高尔作品中的某些章节就能达到这种效果。让我们再次转到郎兰为米德夫人所写的那令人难忘的审判场景。因为在那部诗作以及其他诗作中,解决紧迫社会问题的途径是求助于国王。我再次承认:我已将这种把所有重要事情的解决都仓促求助于国王的倾向称为英国早期历史上的“小鸡综合征”(Chicken Little Syndrome)。
然而,我们不也在中古晚期盛行的文学作品中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阴影吗?但是,有一点似乎是重要的,那就是我们再次认识到了文学作品作为历史证据的价值。如果希望与前景依旧,那么一种新的质疑又出现了,其严厉甚至痛苦的批判直指捍卫正义的王权。虽然《加麦林的故事》是以国王纠正了错误而结束的,然而,直到事情最后解决之前,审判过程还是很令人恐怖的。法庭场景包括对陪审团、法官、郡守的袭击,所有这些人最终都被一位英雄及其忠实追随者绞死,即便是在王室法庭遭受攻击后君主的护佑降临也是如此。一个多世纪之后的罗宾汉的故事,同样反映了司法机构的腐化,只是在国王个人的干预下,司法机构的腐化才得以矫正。毫不惊讶的是,讽刺文学和控诉文学甚至把历史描绘得更为黑暗。那么,重点研究遗留案件就能表明这种批判真有社会基础吗?我们在历史上真能找到与罗宾汉故事中所嘲笑的令人痛恨的官员如出一辙的原型吗?我们也可以再次思考,在1381年起义者眼中,国王如何依然保持尊贵的形象。他未被起义者伤害的原因是,起义者的怒火是冲着国王身边的人去的。因此,这些富有想象力的文学作品难道没有令人信服地印证著名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吗?我们再次找到了一种明确的解释视角吗?
第五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问题可能涉及更为复杂的因素。通过讨论战争与法律、正义、统治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有所收获吗?盎格鲁—撒克逊晚期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类似于亨利二世、爱德华三世或爱德华四世统治时期吗?
当然,所有中世纪国王既制定法律又发动战争,但是,新兴国家实力的增长意味着国王的立法权和战争权是同步增长的吗?或者为了改变总体的社会环境,国王能够在这两种权力上投入不同的精力和资源吗?将人们的智慧运用在威尔士的群山中、苏格兰广阔的土地上,以及爱尔兰和法兰西原野上,从而磨灭人们的热情,通过这种方式来发动对外战争就能够保持国内和平吗?
坦率地讲,在探讨这一问题时,我在思索:对几乎所有形式的战争的道德厌恶,是否阻碍了我们去努力研究一个以战争为荣耀、并将战争视为上帝之恩赐的社会?尽管我希望我能在一定程度上遵循学术的客观性,但是我非常怀疑学者会愿意以各种方式回应我的质疑。然而,我还是想强调,如果我们像对待自己一样来对中世纪国王进行道德评判,那么,我们必须以分析性的中立态度去考察国王的战争行为对王国内外产生的影响。我认为这样的审视不仅要用“显微镜”,也需要用“望远镜”,也就是说,我们无需将对战争后果的分析局限于那个时代的流行观点上。并且,难道学者们不能用“双光眼镜”研究问题吗?其中一个镜头用以窥视我们所要研究的人物,另一个镜头用以放宽视野从而理解我们更广视野中的事物。始终用某一种眼光看问题绝对是无法令人满意的,每一位学者都应该仔细考虑他应该选择和利用什么样的视角。
在我们的视野中,存在许多研究战争的新思路。战争不仅仅是对资源的分配,返乡的士兵可能会对乡村的和平与法纪产生某些影响。士兵们在国外所从事的活动,一旦放到国内,就变成非法的了。那么,他们如何适应国内生活呢?
同样,我们也能够更多地了解当时相当普遍的君主赦免现象,这些赦免通常是非常广泛的,而只有那些在国王发动的战争中有优异表现的人才能获得这种赦免。当(国外)严重的合法暴力使得(国内)非法暴力不再受到指控时,司法文化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呢?在一个对战争习以为常并投入相当多战争资源的社会中,如果原告知道他们无法从被告那里获得补偿的话,难道他们不怒火中烧吗?因为当被告一踏上英国土地的时候,他们手里就握有令人讨厌的羊皮赦免书了。
我所提出的上述问题都是相互交叉的。尽管我们有着悠久的辩论传统,但是我还是希望通过新的整合来更清晰地阐述上述问题。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狭隘的分支学科研究和编年史研究,也不能局限在历史和文学的语境中思考问题。相反,全面地看待问题似乎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转自《历史研究》(京)2010年3期第82~88页
责任编辑:刘悦
分享到: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
上一篇:托勒密埃及的法律与司法实践
最新更新
猜你喜欢
关注我们


 当代时讯
当代时讯  中国历史
中国历史  世界历史
世界历史 历史典故
历史典故  历史百科
历史百科  野史秘闻
野史秘闻  民间故事
民间故事  神话传说
神话传说  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  网站首页
网站首页